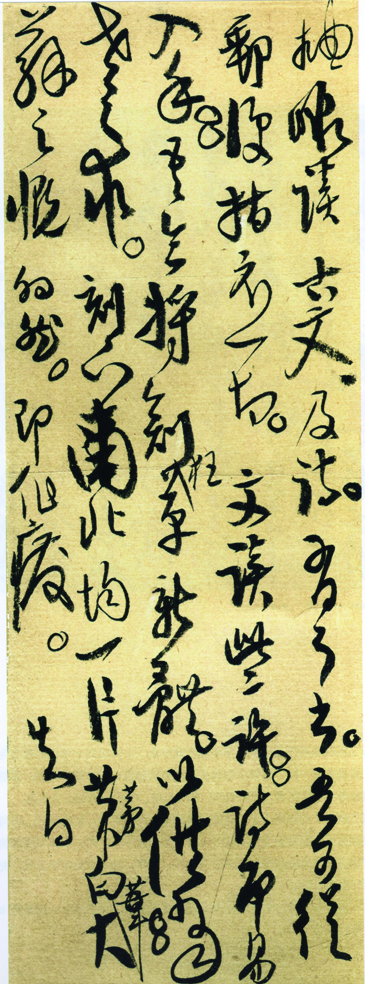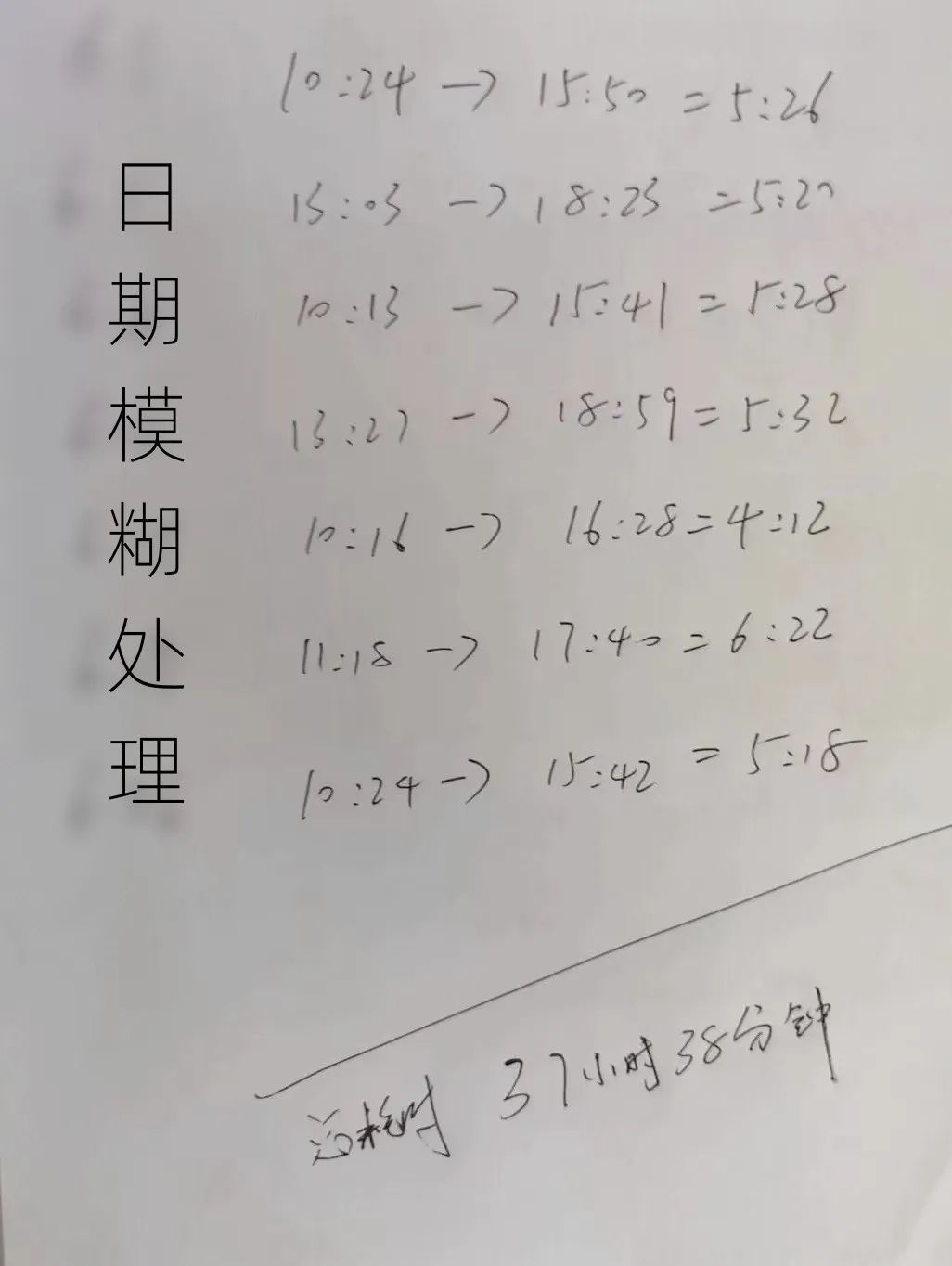前几天无意中看到了一个访谈节目,是北京台的阿龙在与相声演员刘洪忻、李增瑞,还有纪连海以及其他两位嘉宾,我都不认识了。他们谈到说豆汁过去就是穷人吃的,但是遭到了纪连海的反驳,说是据《乾隆帝起居注》中记载,乾隆皇帝雇了两个厨子专门做豆汁,豆汁焦圈,乾隆爷也爱吃。同时也提到了英达自诩为大户人家,不喝豆汁,说都是穷人喝的。其实这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有问题的。
豆汁历史悠久,有传说早在辽、宋时就是民间大众化食品。但其实并没有发现具体的文字记载,根据文字记载大约有300年的历史。乾隆十八年(1753年),有人上殿奏本称:“近日新兴豆汁一物,已派伊立布检查,是否清洁可饮,如无不洁之物,着蕴布募豆汁匠二三名,派在御膳房当差。”于是,源于民间的豆汁成了宫廷的御膳。
每年旧历九月至次年立夏后5天,清宫御、寿两膳房(据记载:光绪年间,清朝宫廷的御膳部门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为光绪皇帝操办饮食的御膳房,一个是为慈禧太后操办饮食的寿膳房和寿茶房。)都要制做豆汁,帝、后酒肉之余,皆饮豆汁以解油腻。据说,咸丰梓宫(灵梓)回銮,东西两太后带领同治帝刚回到宫里,即向御膳房要豆汁儿喝。在民间,豆汁儿的主顾更不分贵贱,凡穿戴体面者在庙会上吃“灌肠”或“羊霜肠”,往往会被人耻笑,唯独喝豆汁儿则不足为耻。同样,有穿戴体统者,如果坐在摊上吃灌肠或羊霜肠,就会被人耻笑,但在摊上喝豆汁则不足为耻。
过去有一则笑话,说齐化门(朝阳门)外营房的旗人都聚在街头痛哭流涕,路人问之,哭者愈痛,谓“豆汁儿房都关了张,岂不要了性命?”笑话归笑话,老北京人尤其是旗人,特别喜爱喝豆汁儿,甚至称之为“本命食”乃是事实。俗话说,老北京旗人有“三嘴”:即所谓“豆汁儿嘴”、“老米嘴”、“卤虾嘴”。这里的“豆汁儿嘴”就是指的是旗人大都喜爱喝豆汁儿。
所谓“老米嘴”就是指的是旗人喜欢吃“老米”,“老米”又被人称为“禄米”、“粗米”。这是源于康熙年间的定例,当时国力鼎盛,官仓粮食甚多,用说书常用的套话来说,就是“米烂陈仓”。这些官仓储粮充实,仓内有大量的陈米积压。久而久之,这些陈米颜色泛红,同时还产生一种“异味儿”。这种“变色生味”的陈米则被人称为“老米”亦有人称“禄米”。之所以又被称为“禄米”,是因为众所周知,在大清朝时北京城里的旗人是自出生就享受官俸禄米的特殊待遇,即所谓的“铁杆儿庄稼”。其享用的禄米基本就是这些仓储老米,所以有人又称之“禄米”,大概这种称谓还颇有些自豪感吧!
据说老米别看发霉变色,可下锅一蒸就会膨胀,显得颗粒饱满,而且口感筋道,更妙的是会有种“奇香”,因此一般旗人家里哪怕有新米,也更愿意吃老米,因为觉得老米更顺口。到了民国时期,这种官仓老米渐渐地没了,旗人的供奉禄米也断了,这时,旗人家庭留存的老米则成了“珍品”。不少旗人家庭把自己家剩下的老米当作宝贝一样地储存起来,平时舍不得吃,只有到逢年过节或招待贵客时,才吃上一顿“老米饭”。这种所谓的“前朝老米”大概延续到北京解放前,即上世纪40年代末,就基本“断顿了”。“老米”这名称也就渐渐地在后人的记忆中消逝了。
至于说“卤虾嘴”指的是“卤虾油”,过去老北京人都喜欢吃这一口,现在已经彻底见不到了,有说法是说:春季将乌虾放入容器,加盐,封严,发酵。加盐的量要达到饱和。10月初,发酵完成。乌虾种类不同,发酵出来的卤虾油颜色也不同,有像香油一样颜色的,有黑褐色的。从原容器中提出来的是发缸水,价格不菲。勾兑出来的是俗称的卤虾油。过去在天津塘沽海边有专门制作这个的,现今已经几乎没有了。
民间卖熟豆汁儿有两种形式:一是走街串巷的豆汁儿挑子,吆唤“开了锅的豆汁儿粥!”买者多是以锅、碗端回家去喝;另一种形式是在庙会集市上摆个豆汁儿摊,设丈余长案,前摆长凳。案上放2—4个大玻璃罩,大玻璃罩内放大果盘,盛着酱黄瓜、八宝菜、酱萝卜、水疙瘩丝等。春季备有爆腌酱苤蓝,冬天备有五香萝卜干丁。对购买细酱菜的顾客供应辣椒油。并代卖芝麻酱烧饼、炸焦圈儿等食品。不要看豆汁其貌不扬,但一直受到北京人的喜爱,原因在于它极富蛋白质、维生素C、粗纤维和糖,并有祛暑、清热、温阳、健脾、开胃、去毒、除燥等功效。
卖豆汁的照例是从粉房将生豆汁趸来,挑到庙上,就地熬熟。前边设个长条案,上摆四个大玻璃罩子,一个放辣咸菜;一个放萝卜干;一个放芝麻酱烧饼、“马蹄”(此系另一种形式的烧饼,状如马蹄,故名。有椒盐马蹄、两层皮的水马蹄之分);一个放“小焦圈”的油炸果。案上铺着雪白桌布,挂着蓝布围子,上面扎有用白布剪成的图案,标出“×记豆汁”字样。夏天还要支上布棚,以遮烈日。经营者通常为一、二人,不停地向游人喊道:“请吧,您哪!热烧饼、热果子,里边有座儿哪!”
《燕都小食品杂咏》中说:“糟粕居然可作粥,老浆风味论稀稠。无分男女齐来坐,适口酸盐各一瓯。”并说:“得味在酸咸之外,食者自知,可谓精妙绝伦。”
《北平旅行指南》(1935年)记载:“一锅豆汁味酸甜,咸菜盛来两大盘,此是北平新食品,请君莫作等闲看。麻花咸菜一肩挑,矮凳居然有几条,放在街头随便卖,开锅豆汁是商标。”
《北京风俗杂咏续编•厂甸竹枝词(锦堂)》亦记载:“豆汁是做绿豆粉条或团粉时剩下的一种液体,经过发酵而成,它那种酸腐的气味常给第一次喝它的人以很坏的印象,可是,假使你能硬着头皮喝它一两次,你就会渐渐品出它的妙来。——‘豆汁燕京素有名,临时设肆赞经营,座中绿女红男满,一片喧哗笑语中。’”
梁实秋在其《北平的零食贩》中写道:“绿豆渣发酵后煮成稀汤,是为豆汁,淡草绿色而又微黄,味酸而又带一点霉味,稠稠的,浑浑的,热热的。佐以辣咸菜,即棺材板。切细丝,加芹菜梗,辣椒丝或末。有时亦备较高级之酱菜如酱萝卜酱黄瓜之类,但反不如辣咸菜之可口,午后啜三两碗,愈吃愈辣,愈辣愈喝,愈喝愈热,终至大汗淋漓,舌尖麻木而止。北平城里人没有不嗜豆汁者,但一出城则豆渣只有喂猪的份,乡下人没有喝豆汁的。外省人居住北平二三十年往往不能养成喝豆汁的习惯。能喝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
喝豆汁必须配切得极细的酱菜,一般夏天用苤蓝,讲究的要用老咸水芥切成细丝,拌上辣椒油,还要配套吃炸得焦黄酥透的焦圈,风味独到。豆汁是用制造绿豆淀粉或粉丝的下脚料做成的北京的风味小吃。生豆汁儿是水发绿豆加水研磨后,通过酸浆法令悬浊液的黏度适度增加,使颗粒细小的淀粉浮在上层,取之进行淀粉的分离(便于增加淀粉的出粉量);中间的液体就是生豆汁。豆汁一般味酸,略苦,有轻微的酸臭味。
一般人喝豆汁,不管它是热还是凉,自然喝不出所以然,而且现今一些卖豆汁的铺子把豆汁熬好以后就放那儿,凉了才再加热,有的索性就不管了,这怎么能喝到正宗的豆汁呢?凉着喝,入嘴便会有泔水味;如果趁热喝,味道就不一样,甜中带酸,酸中有涩,滋味独特;再就着咸菜丝、焦圈、烧饼之类就更有味道了。
唐鲁孙先生在其《中国吃》中也有关于豆汁的记载:“豆汁儿可以说是北平的特产,除了北平,还没有听说哪省哪县有卖豆汁儿的。爱喝的,说豆汁儿喝下去,酸中带甜,其味醇醉,越喝越想喝。不爱喝的说其味酸臭难闻,可是您如果喝上瘾,看见豆汁儿摊子,无论如何也要奔过去喝它两碗。北平卖豆汁儿的有挑担子下街的,有赶庙会摆摊子的,只有天桥靠着云里飞京腔大戏旁边奎二的豆汁儿摊,那是一年三百六十天都照常营业的。
他姓奎自然在旗,云里飞时常拿奎二打哈哈,他说奎二摊子有三绝:第一,各位主顾只要往摊子边一坐,您就算是皇上御驾光临啦。因为天桥一带都是土地,一起风,尘土飞扬,豆汁儿碗里,等于洒了一把香灰,辣咸菜里加上了胡椒面,您说怎么喝。所以人家奎二每天摆摊儿之前,先用细黄土把摊子四围填满拍平,然后随时用喷壶洒水,您坐下喝豆汁儿,给您黄土垫道净水泼街,您不是临时皇上了吗?第二,奎二的辣咸菜那是谁也没法子比的。大家都说西鼎和酱菜切得细,人家奎二的咸菜丝儿,比起来更细更长。第三,奎二的豆汁儿酸不涩嘴,浓淡适口,豆汁儿一起锅,不管买卖多冲够卖不够卖,绝不搀水。虽然云里飞是给朋友宣传,可是他说的都是实情一点儿也不假。”
据金云臻先生《饾饤琐忆》记载:“提起北京的豆汁,真是赫赫有名。是一种极富于地方风味的特别饮料。其他地方,没听说过。近如天津,有些小吃大同小异,至少我没见过豆汁。北京老土著,几乎人人嗜饮豆汁。除土著外,只要在北京常住几年的人,也会对豆汁发生好感的。
豆汁是一种饮料,喜欢喝它的人,视同珍味,不喜欢喝它的人,嗅一嗅都避之不遑的。实际上豆汁虽不是什么珍馈美味,但在一饮之后,它有一股微酸回甘的鲜味,和吃橄榄一样,颇足诱人。作为饮料,它又与粥、泡饭起同样的效用,可以果腹,而且酸中带鲜,又有甘味,不能把喜欢食用这种饮料的人,都看成‘嗜痂之癖’。
豆汁是粉房做绿豆团粉的副产物。北京人做菜用以著黏的淀粉,都用绿豆粉,名叫团粉,和别地方用菱粉、藕粉、山芋粉、荸荠粉一样。团粉粉质细腻、洁白,凝性又好,价钱又便宜。制团粉的作坊叫作粉房。北京各处街道大部有粉房。制团粉时把绿豆磨成浆,加一定量的白玉米粉,放置大桶内沉淀。沉淀到一定时间,大桶内的粉浆上层是清水,倾出倒掉。中层是灰绿色的薄浆,就是生豆汁。底层才是洁白的淀粉,是做团粉的原料。生豆汁批发给卖豆汁的小贩,居民也能买到,买回自己烧成熟豆汁,可当粥吃。
小贩批来生豆汁,要经过细致的加工。考究的还要二次沉淀,去其杂质污物,下锅加适量水煮熟。熟豆汁颜色也呈灰绿,很暗淡,由于沉淀已起发酵作用,所以带酸味,而且微有馊气。小贩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口中呛喝:‘豆汁来~开……锅——’声音敞亮而拉长尾音,以引动买主。豆汁所以倍受欢迎,不只因它别有异味,还在于经营方法。小贩卖豆汁传统的规矩是,只要喝他卖的豆汁,便奉送咸菜。自制的咸菜不过是萝卜丝、芥菜疙瘩丝,配上芹菜、碎辣椒等腌成的,毫不足奇,但它的辣味极重,与酸豆汁很合宜。买一个烧饼,花一个铜板喝一碗豆汁,佐以辣咸菜,亦是其乐无穷。
豆汁摊不问是挑担,或庙会集市设摊,设备都一样。一副挑子,一头是火炉大锅,与卖老豆腐、面茶等食品一样;另一头在木圈上放一只固定的大木方盘,中置碗盏、筷子筒,四周放置大的磁盘或铁盘四只,满盛咸菜丝。方盘下挂着几只小板杌,喝豆汁的人可以任意取下坐在方盘周围慢慢吃。
豆汁在北京虽到处皆有,但质量却分高低。当时北京最有名的豆汁,要属琉璃厂厂甸摆摊的张家豆汁。大约在清末民初出现,己有二三代的传人了,摊主张进忠。他家豆汁所以出名,除了烧煮得法,主要在于选料极精,专用前门外四眼井一家出名的粉房的豆汁。就连辣咸菜的配制,也很考究,以是闻名全市。
如果一个人头一次尝试豆汁的滋味,虽不能说作三日呕,但也不会立即产生好感,可是一尝再尝之后,常被它那特有的回甘之味所征服,由不可耐到可耐,由可耐到非此而不欢,慢慢地就被豆汁‘俘虏’了。北京人立春要吃春饼,吃春饼必用豆汁。因它有助消化、去油腻的作用。一般人于长日无俚,囊有余资,下午喝一碗豆汁,买一副烧饼油条,辣咸菜一小碟,只花几个铜板(按现在说不超过四五分钱),就是一味绝妙的大众化点心。同是一饱,与广州、上海、成都那种坐茶馆,吃点心,丰腆之间,是不能同日而语了。”
周绍良先生在其《齿留余香回忆京城》记载:“‘豆汁’不是从豆浆演变来的,它是制作粉条的下脚料,有人专门把它收集来,再行加工,成为一种灰色的流质,闻起来有一点馊味,尝起来带一点酸头。外地人很不习惯这种食品,但本地人却嗜之极深。
制粉后的下脚料,经过发酵变成酸味,再加熬煮,便成‘豆汁’。
熬煮豆汁,不能一次下锅,必须少量一次一次地续,不能叫它开锅,熬豆汁是陆续往里添的。这也是一宗手艺。有的熬好之后,自己下街去卖,也有的整个趸给大的豆汁摊。
北京卖豆汁的很多,各个庙会都不止一两摊,还有每天早上,提着桶用小车拉着走街串巷卖的,可见吃豆汁人之众多。
一般大摊都是在庙会或市场里拉一长摊,桌上摆好一大碗咸菜,水疙瘩细丝,另外许多小碟也摆着这水疙瘩丝,这是供给一般喝豆汁的客人,是不要钱的。另外还有一些小的碟子,装的是各种酱菜丝,如酱瓜丝、酱笋、酱白菜、八宝菜,这是专门为另一种人预备的,要花钱买的,据说有人喝过豆汁之后,感到醋心,吃过咸菜就过去了。
北京最有名的豆汁摊有四家,一处是天桥‘舒记豆汁’,另外两处是东安市场的‘豆汁徐’和‘豆汁何’,还有一处在琉璃厂,叫‘豆汁张’。这四家比较起来,‘豆汁张’更受人欢迎。他们是父子经营,老头张殿臣,儿子张进忠,都很老实厚道,待客热情,豆汁的味道也醇正。铺一个长摊在琉璃厂新华路口,声名远扬,很多人远道而来,尤其是梨园人士。
早上的主顾是一些遛早的和干活的瓦木匠一类人,中午则是师大的老师们和一批老北京,还有一些学生们,有的就着贴饼子单买一碟‘腌芥蓝丝’当一顿午饭,过午之后就是这些梨园行的人了。也有成桶提回家喝的,都是些常年老主顾。喝两碗豆汁,吃一个焦圈的朋友,也都是熟人。一直到晚上7点多钟收摊回家。”
穆儒丐先生在其《北京梦华录》中亦记载:“当初太平年间,在我小的时候,豆汁的售卖,是有节令的。由旧历正月初一起,生豆汁便上市了,直卖一春天,一入夏就不卖了。现在因为嗜者日广,把节令已然打破,四季咸宜。……岁末开始,家家都要大吃大喝,未免油腻过盛,必得拿消火解毒之品来调剂,酸豆汁,在人人脑海正盼着,所以听见一声甜酸豆汁,便争先来买。”
常人春在其《老北京的风俗》中记载:“有人说,豆汁是老旗人的吃食,其实喜欢喝豆汁的并不局限于民族,也不拘贫富。旧时,有穿戴体统者,如果坐在摊上吃灌肠或羊霜肠,就会被人耻笑,但在摊上喝豆汁则不以为耻。”
陈鸿年先生在其《故都风物》中记载:“故都的小吃千百种,多得数不清,说不完,而最经济、最平民化,恐怕还算豆汁儿了。
一大枚一大碗的豆汁儿,摊儿上的咸菜,是奉送白吃的,爱吃辣的,还可以白饶给您几滴儿澄红的辣椒油。稠糊糊,热腾腾,酸不叽儿,香喷喷的。如果再吃上两套烧饼麻花儿,作为下午的点心,真来劲!
大一点儿的豆汁摊儿,用的案子,用水刷得露着白碴儿,一转圈,围着阴丹士林布,周围放一圈长板凳,看着这份干净漂亮,就不用提啦!
案子上,不远放个一尺二寸的大瓷盘子,放一转圈儿,盘里放着咸菜丝,切得细细的,堆得像个塔尖儿;但是不准动手,他会另拿个三寸碟,夹一些给您,这等于是豆汁摊儿的幌子。
另外有个大盘,放着:酱瓜儿、酱白菜、大头菜、咸辣椒、十香菜。这就需要另拿钱买了,一大枚可买两样儿。
在豆汁摊儿上喝豆汁儿,一大枚一碗。可是要买生的豆汁儿,回家自己熬着喝,可就贱多了。单有挑着木桶,串胡同儿卖生豆汁儿的。在午饭已过的两三点钟,挑子放在地下,用手一握耳朵:‘粥啊!豆汁儿粥啊!’
您拿个砂锅,去买吧!一大枚,能给您三四大勺儿,足有大半锅,熬开了,足够三四个人喝的。再在炙炉儿上,烤点儿剩饼,烤些剩窝头片儿,炒一盘咸菜,您不是说这是穷吃吗?今天如果真有,吃上还真没有‘散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豆汁儿配焦圈这也是后来的事情了,原本配的是烧饼夹焦圈。遥想当年的豆汁儿及其搭配,比起现在的所谓标准搭配豆汁儿、焦圈、一小碟咸菜来,自不可同日而语了。
现在很多人在说,豆汁儿不是味了,诚然,笔者也去问过,人家伙计说了,材料不对了,所以做不出原本的味道来了。再就是现代的人们口高了,对这些东西也不大在意了,质量自然也就越来越差了。再就是喝者不得法,自也品不出其中的甘甜了。
老北京的各种美食现而今随着社会地不断发展而渐行渐远,留给我们的原汁原味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正如一位资深美食专家所说的那样,现在不是在拼质量,而拼的是谁更会忽悠。那些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得比不上那些只会用嘴忽悠的人,也就无怪乎生活的品质越来越高,食品的品质却是越来越差了!
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lzxmw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