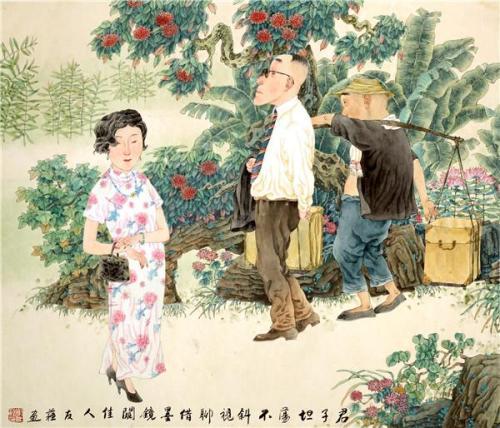李穆很犹豫,他之所以犹豫,因为他无论如何也算不明白这笔账,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了,他不能准确的判断杨坚和尉迟迥会是谁胜谁负,他也不知道倒向谁,会让李氏家族获得更大的利益。
就在李穆犹豫不定之际,杨坚的使者柳裘抵达了晋阳。我们不知道柳裘跟杨坚说了些什么,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柳裘出色的完成了他的工作,在他一番发言后,李穆就转忧为喜——甚悦。然后,李穆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抉择——将尉迟迥的来使锁拿,送往京师。
不久后,李穆迎来了杨坚派来的第二个使者——他的儿子李浑。李浑是杨坚打出的亲情牌,因为,杨坚也不能确定柳裘是不是可以真正说服李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必须用最大的诚意,将李穆争取在自己手中。
此时的李穆终于完全下定了决心,他让李浑给杨坚带去一个熨斗,而且,还送给了杨坚一句话——愿执威柄以尉(慰)安天下。另外,李浑还给杨坚带来了另一件东西——十三环金带(这是皇帝所用的服饰)。

这是李穆至关重要的一个暗示,事实上,李穆如今倒向杨坚,已经是做了通盘的考虑。因为,杨坚主政,不仅仅只有此次跟尉迟迥较量这一件事,更重要的是,这位蛰伏了多年但政治手腕强硬的国丈,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北周而代之。李穆送杨坚金带,这意味着,李穆正式宣布支持杨坚未来可能的篡位!
李穆之所以一下子表那么多态,表态表那么远,当然有他的道理。《教父》中维托·克里昂说,当你向别人施舍恩惠时,你就要表现得很有感情。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你决定一件事情时,要么不做,要做,那就一步到位。
李穆决定一步到位,他要让施恩变的有感情,他认为,杨坚会因为他的雪中送炭而感激他,而他们李家,也会在未来的政治拼盘中,得到尽可能多的份额。
李穆是对的,杨坚非常激动,激动地立即让李浑马不停蹄再跑了一趟——去哪呢?去韦孝宽的大营,去告诉韦孝宽李穆对此次事件的态度!
得到了李穆的支持,杨坚在跟尉迟迥的较量中,已经握有一个十分有力的砝码。而李穆做出决定后,也很快以族长身份通告全族,统一了意见——他有个侄子李崇当时任怀州刺史,正打算响应尉迟迥,在得知叔父的选择后,也只能抱怨几声(阖家富贵者数十人,值国有难,竟不能扶倾继绝,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然后,服从大局,倒向杨坚。
光有一个李穆,够了吗?还不够,杨坚还需要说服另一个人,同样能量强大的一个人——于翼(时任幽州总管,幽州是今北京)。
于翼是于谨的次子,而于谨,则是北周八大柱国之一,在宇文泰病故,朝内纷纷不定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帮助宇文护稳定了局面,立下了殊功;因此,于谨可谓是北周立国第一功臣。在北周建立后,于谨家族满门富贵,风头一时无两。
当然,日中则昃,月满则亏,于谨家族如此强盛,到最后也不免遭到宇文氏的打压——于谨的次子于翼,在宇文护时代就饱受排挤(主要是因为宇文邕当时竭力拉拢于翼);而三子于义,更是因直言劝谏,而差些被宇文赟治罪。
如今杨坚上台,深知于氏家族能量的他,一开始就极力拉拢于氏——很快,杨坚便将于谨的长子于寔进位为上柱国,任命为四大辅臣之一的大左辅。当时,在朝内的三公四辅中,只有两个人是不具有宇文氏皇族背景的,一个自然就是前文所说的“太保”李穆,而另一位,便是刚成为“大左辅”的于寔了。
杨坚投之以桃,于氏家族自是报之以李。尉迟迥的使者,也很快就到了幽州,想要说服于翼,但是,于翼丝毫不为所动,立即将使者执送京城。
于翼的这个表态有多重要?事实上,尉迟迥宣布造反后,便跟东北的高宝宁联络,意图跟突厥合作,一块南下;但是很可惜,在尉迟迥跟高宝宁之间,横着一个于翼,所以,这种合作,也只能成为纸面上的意淫了。
另一个为杨坚肝脑涂地的于家子弟,是于寔的儿子于仲文。
当时于仲文是东郡(今河南滑县,当时黄河未改道位于黄河以南)太守,跟徐州总管源雄一起,受到了尉迟迥邀请,二人都严词拒绝。同样是拒绝,于翼拥有足够的底气,因为他拥有幽、定七州六镇,尉迟迥虽然不爽,但也不敢对其轻举妄动,但是,于仲文却立即遭到了尉迟迥势力的夹击——当时宇文威从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古黄河渡口),宇文胄从石济(今河南省卫辉市东古黄河渡口),先后渡河,夹攻东郡。

于仲文不过是一郡太守,芝麻绿豆大的官,人家尉迟迥是看在他姓“于”的份上,给他个面子;如果于仲文不要面子呢?那就只能对不起咯。
于仲文对付宇文威倒还尚可,然两路夹攻,便已无法招架,只能放弃东郡,率数十骑溃围而出,东奔长安,但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于仲文是走了,老婆孩子还在——为了这次拒绝,于仲文付出了三子一女的代价。
于仲文好不容易才跑到长安,当时,他所带领的数十卫士,已经伤亡殆尽,所剩无几,而他自己也已是狼狈不堪。当于仲文见到杨坚时,杨坚将其引入卧室,为之垂泪,于是“赐彩五百段,黄金二百两,进位大将军,领河南道行军总管”。
于家对杨坚此次平定尉迟迥之乱有多大贡献?请看于仲文的自述:
曩者尉迥逆乱,所在影从。臣任处关河,地居冲要,尝胆枕戈,誓以必死。迥时购臣位大将军、邑万户。臣不顾妻子,不爱身命,冒白刃,溃重围,三男一女,相继沦没,披露肝胆,驰赴阙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
(充满感情的回顾了当日尉迟迥叛乱时,自己是如何坚定的站在了杨坚一边,又是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得以九死一生的回到长安,而当时的杨坚,看到于仲文如此表现,又是如何的对其嘉奖重用的)
于时河南凶寇,狼顾鸱张,臣以羸兵八千,扫除氛昆。摧刘宽于梁郡,破檀让于蓼堤,平曹州,复东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围,殄徐州贼。席毗十万之众,一战土崩,河南蚁聚之徒,应时戡定。
(当自己被任命为河南道行军总管后,他率领八千人马,开始扫荡叛党。先后击败了梁郡的刘宽,蓼堤的檀让,而后又相继平定曹州,收复东郡、安城、武定、永昌,解除叛党对亳州的包围,歼灭徐州的乱军。在自己的一番努力下,席毗十万之众,终于遭到覆灭,河南的叛乱局面,就此得到平定)
当群凶问鼎之际,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总驭燕、赵,南邻群寇,北捍旄头,内外安抚,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斿黑水,与王谦为邻,式遏蛮陬,镇绥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敌,乘机剿定,传首京师。王谦窃据二江,叛换三蜀;臣第三叔义受脤庙庭,龚行天讨。自外父叔兄弟,皆当文武重寄,或衔命危难之间,或侍卫钩陈之侧,合门诚款,冀有可明。
(在整个叛乱过程中,不仅是我本人,我们于家全体也对朝廷做出了卓越贡献。我的二叔于翼,当时被叛党和突厥夹在中间,但是,正因于翼的分兵拒之,才让两股力量不能合兵一处,稳定了华北的局面。我的五叔于智则帮助平定了西蜀王谦的叛乱。我的兄长于顗在淮南立下大功。我三叔于义也参与了对王谦的讨伐。除此之外,于家满门忠烈,都对平定叛乱做出了卓越贡献)
我想,于家的支持对杨坚的意义,我们也不再需要过多废话了。
有了李穆家族和于翼家族的力挺,杨坚就有了平定尉迟迥的最大底气。
然而,杨坚所要对付的敌人,又岂是尉迟迥一人?就在尉迟迥叛乱如火如荼之际,京城内迎来了又一波危险的敌人——六月,五王皆至长安。
对于五王的进京,历史上向来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是被杨坚弄回来的。《资治通鉴》就有此类描述:
陈王纯时镇齐州,坚使门正上士崔彭征之。彭以两骑往止传舍,遣人召纯。纯至,彭请屏左右,密有所道,遂执而锁之,因大言曰:“陈王有罪,诏征入朝,左右不得辄动!”其从者愕然而去。
这种说法未免是过于侮辱了五王的政治能量。如果宇文纯这样的亲王,都能随便被两个人就在自己的地盘给捆了,而且手下人还不敢妄动,居然作鸟兽散,那宇文赟又何必如此担心,非把他打发到自己的封国去呢?
事实上,五王既不可能是杨坚骗回来的,也不可能是杨坚绑回来的,他们同时回归,只存在一种可能性——接到了宇文赟的遗诏。
这是历史上对五王进京的第二种看法,小的我觉得,是比较符合逻辑的。
宇文赟虽然是个暴君,但是,我们也得承认,这个暴君在玩弄权术方面很有一手,至少,在他的任内,没有出现过前朝宇文护这样的权臣。没有权臣就意味着,他的传位过程,本来可以顺利得多……
宇文赟重用的人物,虽然都不是什么好咖,但多是些没有政治根底的寒门子弟,以至于当他病重时,他的宠臣刘昉、郑译等辈,都无力独撑大局,非得让杨坚去捡这便宜。当然,杨坚能捡到这便宜,也有些机缘巧合,在宇文赟的整肃下,杨坚本已预感前途渺茫,要出藩以求自保了,但是,偏偏杨坚得了“足疾”,而宇文赟又偏偏不早不晚的病倒了……这一切,也只能用当日宇文邕对王轨所说的话来概括——必有天命在,将如之何?
古今中外很多事情,都是“人算不如天算”,很多达官显贵很迷信,动不动占卜算卦请人看相,也并非全无道理。以杨坚而言,他的发达,实在是“三分能,七分命”最好的写照,堪称中国历史最幸运的开国皇帝。
宇文赟先前让五王出藩,虽然有杨坚所谓“羽翮既剪”的弊病,但是,宇文赟也有自己的考虑。因为宇文护的关系,宇文赟一直非常害怕宗室擅权的现象,所以,他上台后的第一步,是干掉宇文宪(尽管宇文宪这位亲王实在没有反心,实在对朝廷忠心耿耿),而他让五王出藩,实际也不过是延续了诛杀宇文宪的政治思路——“强干弱枝”,避免在京城出现“下一个宇文护”。
“弱枝”是为了“强干”,但是,“强干”这件事,也是多重因素决定的,宇文赟千算万算,却漏算了最重要的一步——自己的寿命!
杨坚之所以比宇文赟更高明,就因为算先一步——视其相貌,寿亦不长。
就因为多算这一步,杨坚才会想要在出藩之前先等等看,他的“足疾”才会如此恰到好处,他才能在诸多显贵中“幸运”的脱颖而出,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这也是托孤没有尉迟迥的原因之一。
所谓“幸运”,从不会是无源之水,机遇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最“幸运”的杨坚,其所展现的,岂不正是高超的“预见机遇”、“把握机遇”的能力?
宇文赟在最初暴病之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所击倒,直到十几天过去了,一天又一天,他的身体日渐虚弱,宇文赟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他这才意识到,京城内没有得力的亲王坐镇,会有怎样的恶果!毕竟,亲王这东西,既可能是皇位的争夺者,也可以是皇位的捍卫者啊!
“强干弱枝”这一套彻底失败了,自己儿子宇文阐太小,这个“干”强不起来,而他把“枝”给削弱,也只会让这个虚弱的“干”,暴露在一堆野心家面前。如之奈何?宇文赟认为,为今之计,也只能亡羊补牢了,在五月二十二日,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的宇文赟,下发了诏书,要求五王进京勤王,保护幼主!
同时征召五王,这也是宇文赟一贯玩弄权术的体现,因为对于这五王,既要用,又要防,自己的儿子太小,无力防,那就让五王各自防着对方吧。
宇文赟的这个安排,就是传说中的“制衡术”。
如宇文赟这样的托孤安排,后世也有类似的例子。
清朝初年,顺治英年早逝,民间也有说顺治出家了,嗣子爱新觉罗玄烨年仅八岁,因此,顺治给玄烨安排了四个顾命大臣——首辅索尼、次辅遏必隆、三辅苏克沙哈、四辅鳌拜。
顺治这样安排,本来非常高明,既维持了八旗之间微妙的政治平衡,又尽力避免了一家独大,威胁皇权——因为,首辅索尼当时已经年迈;而次辅遏必隆,又是个无可无不可的墙头草;三辅苏克沙哈,地位尴尬,是睿亲王多尔衮的部下;最凶恶的鳌拜,虽号称“满洲第一勇士”,但位次最低,谅他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后事安排成这样,苦心孤诣的顺治本可以含笑九天,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令顺治没有想到的是,最凶恶位次最低的鳌拜居然能够在四辅臣中脱颖而出——原因?因为索尼年迈而又奸猾,在没收到皇室的政治献礼前,拒绝表态,等他得到了皇室的大礼(孙女被纳为皇后),准备恭请康熙亲政时,却已经时日无多;遏必隆是个墙头草,很不幸,这次他倒向了鳌拜,作为次辅,却甘心做小;苏克沙哈有能力,但地位实在尴尬,能量有限,最终被鳌拜击倒……于是鳌拜专权!
事实证明,“制衡术”实在是个很高端的技术活,光靠在脑袋里进行模型推演,往往是不够的。顺治很不幸,把“制衡术”玩砸了,给儿子康熙留下了鳌拜这样凶恶的敌人;但是,“玩砸了”,只能说明功夫不到家,并不能说明“制衡术”本身有问题——毕竟,同一套太祖长拳,让一般人来打,只是平平常常,但要让英雄人物乔峰来打,却能在聚贤庄力敌天下豪杰。
“制衡术”本身没问题,宇文赟让五王顾命也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他实在撑的不够久,两天后,五王还一个都没进京,他就已经一命呜呼了……
于是,顾命大臣的位置立即换了人,蛰伏了许久的杨坚一鸣惊人,脱颖而出,而当六月份,五个亲王先后进京后,他们才赫然发现——朝政已非啊。
如果说外部的尉迟迥,是杨坚控制“国内”局势的最大对手,那么,京城的五王,就是杨坚控制“朝内”局势的最大对手。一场大战,无可避免。
关于这场大战,《资治通鉴》写得绘声绘色,我们也不免细细看来:
五王虽然是最大对手,但率先倒霉的,却是毕王宇文贤。这位“毕刺王贤”,是明帝宇文毓的儿子,也就是宇文阐的叔叔辈。
《资治通鉴》对此事件一句话带过:雍州牧毕刺王贤,与五王谋杀坚,事泄,坚杀贤,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谋不问。
《周书·毕刺王传》对此事件倒是略为详细:贤性强济,有威略。虑隋文帝倾覆宗社,言颇泄漏,寻为所害,并其子弘义、恭道、树娘等,国除。
显然,《资治通鉴》和《周书》的说法是有矛盾的——《资治通鉴》着重一个“谋”字,用法学术语说,这叫犯罪未遂(犯罪已经启动了,但由于犯罪人以外的客观因素,没有能够得逞);而《周书》着重一个“言”字,用法学术语说,这叫犯罪预备(已经有犯罪动机了,但还没付诸实施);朋友们,犯罪未遂和犯罪预备,这可是天差地别的。
到底谁的说法更可靠呢?小的我觉得应该是《周书》。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杨坚是个政治经验丰富的老屁股,如五王这样的危险人物进了京,杨坚第一步会做的,当然是派人严密监视,限制五王的行动自由,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五王还能跟毕王搭上线,那杨坚也就不用混了。
所以,毕王或者有猜疑杨坚的可能,如《周书》所说,“虑隋文帝倾覆宗社”,但是,在杨坚夺权后制造的政治高压气氛下,如他这样的危险人物,自然是得不到跟其他危险人物碰头的机会的,他所能做的,也就是骂个街了。
当然,杨坚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物,哪怕是骂街,也是不允许的,尤其是亲王骂街,所以——只能对不起你了。
诛杀毕王贤,杨坚还有个用意,那就是警告进京的五王——你们给我注意点,如今京城哥们我说了算,别不识相,否则,毕王贤就是你们的下场!
当然,打一大棒,还要给一甜枣,杨坚还是对五王做出了补偿:因诏五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用安其心。
据《资治通鉴》说,不管是大棒还是甜枣,似乎都未能“安其心”,五王还是数次谋划了刺杀杨坚的阴谋:
赵僭王招谋杀坚,邀坚过其第,坚赍酒淆就之。招引入寝室,招子员、贯及妃弟鲁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于帷席之间,伏壮士于室后。坚左右皆不得从,唯从祖弟开府仪同大将军弘、大将军元胄坐于户侧。
(宇文招密谋诛杀杨坚,所以邀请杨坚来做客,然后把杨坚请入了寝室,并让自己的儿子、小舅子们佩刀而立,站在左右,同时还设下了诸多埋伏。而杨坚的左右呢,都被赶了出去,只有杨弘和元胄两个人保护杨坚。)
胄,顺之孙也。弘、胄皆有勇力,为坚腹心。
酒酣,招以佩刀刺瓜连啖坚,欲因而刺之。元胄进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诃之曰:“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叱之使却。胄嗔目愤气,扣刀入卫。招赐之酒,曰:“吾岂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伪吐,将入后邠,胄恐其为变,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伪称喉干,命胄就厨取饮,胄不动。
(酒酣耳热,宇文招开始动手,首先用佩刀刺瓜给杨坚吃,想要借此机会一击毙命。此时元胄站起来表示相府中有事,要先回去,结果被宇文招厉声呵斥。元胄非但没有被吓到,反而更加精神抖擞,扣刀入卫。宇文招见元胄是狠角色,一改先前的嚣张,开始安慰起元胄了,说自己没有别的心思,你也不用太多疑。宇文招数次假装要呕吐,退入后宅,但元胄害怕宇文招设伏,所以屡屡扶着他上坐。宇文招又称自己口干,要元胄去厨房拿饮料,元胄还是不为所动。)
会滕王逌后至,坚降价迎之。胄耳语曰:“事势大异,可速去!”坚曰:“彼无兵马,何能为!”胄曰:“兵马皆彼物,彼若先发,大事去矣!胄不辞死,恐死无益。”坚复入坐。
(此时,滕王宇文逌也过来赴宴,杨坚亲自迎接。元胄对杨坚耳语道,事情有蹊跷,咱走吧。杨坚表示,他们又没兵马,能干啥?元胄说,兵马都是他们家的,他们如果先发制人,我们就完了。我不怕死,怕白白的送死。杨坚不听劝告,继续入坐。)
胄闻室后有被甲声,遽请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坚下床趋去。招将追之。胄以身蔽户,招不得出;坚及门,胄自后至。招恨不时发,弹指出血。
(元胄听到外边有异动,再次请辞,说相府有事,必须走了,于是扶着杨坚下床急速离开。宇文招想要追击,元胄则单枪匹马,用身体挡住了通道,宇文招出不去,等到杨坚到达门口,元胄才赶来。宇文招痛恨阴谋失败,把指头都捏出了血。)
壬子,坚诬招与越野王盛谋反,皆杀之,及其诸子。赏赐元胄,不可胜计。
(不久后,杨坚说宇文招和宇文盛谋反,将其满门抄斩,然后大赏元胄。)
周室诸王数欲伺隙杀坚,坚都督临泾李圆通常保护之,由是得免。
(此后,北周宗亲多次想要谋杀杨坚,杨坚得到李园通保护,幸免于难)
看到这一段描述,大家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没错,《史记·项王本纪》有类似故事——大名鼎鼎的鸿门宴。我们不妨用角色对应的办法一观其相似处:
杨坚自然是刘邦,而且是警觉性极差的刘邦:
元胄劝他走,他还不走,一脸嘬死相;而刘邦在听了樊哙的“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的发言后,就立即撤了,而且还是抄小路走的(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彊、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留了个张良扫尾;
项羽的角色没有,范增和项庄的角色被融为一体——均为宇文招:
“招恨不时发,弹指出血”,这是范增的戏份;范增在项羽错过了诛杀刘邦的绝佳机会后大怒,将张良所献的一对玉斗用剑击碎,然后叹气道:“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招以佩刀刺瓜连啖坚,欲因而刺之”,这是项庄的戏份;在饮宴的时候,范增曾暗示项庄舞剑助兴,伺机干掉刘邦,“项庄拔剑起舞”;
张良的角色没有,项伯和樊哙的角色也被融为一体——均为元胄:
樊哙在鸿门宴是个关键角色,在项庄舞剑后,张良去找他,说:“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也!”樊哙于是进场,史记对此描述的极为生动: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乡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元胄也不例外——元胄进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诃之曰:“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叱之使却。胄嗔目愤气,扣刀入卫。
樊哙在进来后,项羽请他喝酒,又拿了个生猪给他,他拿刀割着就吃,英雄风范尽显,后来一番慷慨陈词,逼得项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位元胄也不例外,进来后,宇文招也请他喝酒,还跟他道歉——招赐之酒,曰:“吾岂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
后来樊哙劝刘邦撤退,说下了那句著名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经典名言;元胄倒是也劝了,而且劝了多次,可惜杨坚都不听……
至于项伯的戏份,在项庄舞剑后,项伯也起身舞剑,以身遮蔽刘邦,这里元胄有两处类似场景——其一、招伪吐,将入后邠,胄恐其为变,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伪称喉干,命胄就厨取饮,胄不动。其二、胄以身蔽户,招不得出;坚及门,胄自后至。
《资治通鉴》的这段描述跟《史记》中的鸿门宴实在太过相似,以至于,我们只能说,当时的史学家也是些无聊的“山寨流”,编故事一点都没创意。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如果杨坚果真是后来得天下的阴谋家,那么,鸿门宴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刘邦之所以要赴鸿门宴这个龙潭虎穴,是因为他封闭关门,惹恼了比他强得多的项羽,不去是躲不开一场浩劫的)。杨坚非但不会去鸿门宴,而且,真要有鸿门宴的情节,他也不该是刘邦的角色——毕竟,很明显,当时的京城,已经处于杨坚的控制下,比之五王,他是当然的强者。
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隋书·高祖纪》很诚实,道出了相对真实的内幕:五王阴谋滋甚,高祖赍酒肴以造赵王第,欲观所为。
原来,这场“鸿门宴”,压根不是宇文招邀请的,而是杨坚亲自去的;既然是亲自去,肯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当然不可能会有那么多险象环生的离奇情节。当然,阴谋依然是阴谋,只不过,阴谋的导演不是宇文招,阴谋的名称,也不叫鸿门宴;这是一场杨坚亲自策划导演并出演的冤案,这场冤案的内容叫做——说你反,你就反,不反也反;有中国特色的“被造反”。
当然,最能表现这次冤狱核心精神的,还不是宇文招,而是另一个人——宇文盛。宇文盛在这个事件中干了些什么呢?答案是,什么都没干——拍成电影的话,连露面都没有,更甭说台词了。然后呢?然后他也就“被造反”了,再然后,他就一家老小都被杀了个精精光了……
什么叫躺着也中枪?这就叫躺着也中枪!
五王去其二,这是杨坚对宇文氏亲王的第二波清算,跟第一波清算一样,打一巴掌,要“揉三揉”,于是,次日——周主封其弟衍为叶王,术为郢王。
好吧,宇文阐当年才七八岁,他的两个弟弟被封为亲王,这两个弟弟能有几岁呢?能给杨坚制造麻烦吗?所以嘛……
有没有第三波清算呢?有,不过是几个月之后了,当时朝廷内外的局势都已经相当稳定,于是,其余三王分别在十月和十二月遭到最终整肃。
至此,五王一个不剩,均为杨坚所杀。
此时的宇文赟,在九泉之下,又当作何反应呢?
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lzxmw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