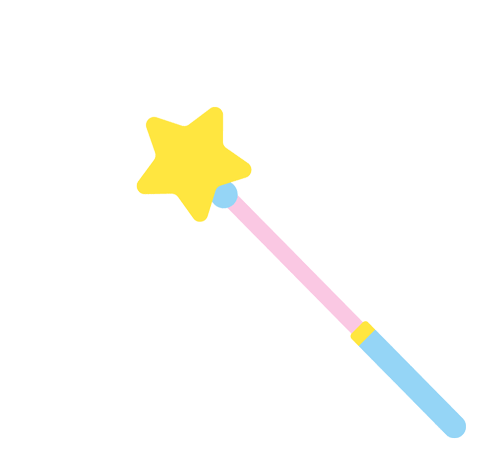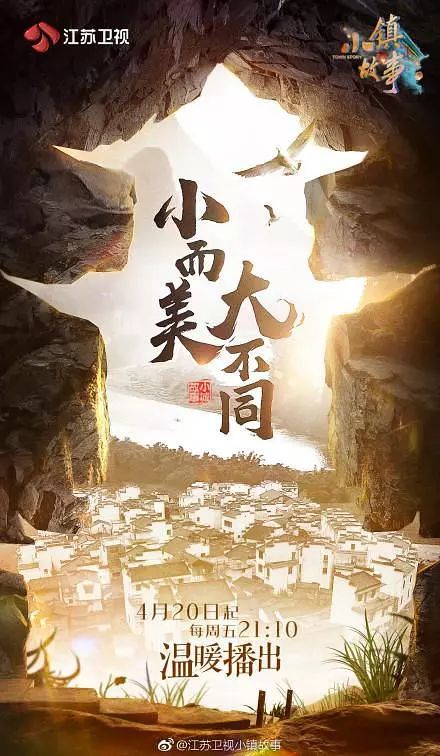#精品长文创作季#
文/松陵笑笑生
欢迎关注“松陵笑笑生”,我将持续为您奉献人文领域优质文章,您的支持是我创作动力。
明代《千秋绝艳图》(局部)
刘向作《列女传》开为女性修史之滥觞。此后《后汉书》首列《列女传》,魏、隋而降,《列女传》遂成为历朝正史之必备。
然而,以男性为主导的古代历史,女性入史何其难哉!《后汉书》自己定下《列女传》入选标准是:
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
所谓贤妃、哲妇、高士、贞女,莫不倾向于钟鸣鼎食之家、达官贵 人之门。深处社会底层的女性,用一生血泪换得个“贞女”名头,也不一定能在史书中留下自己的姓氏。
伟人年轻时代曾感叹,为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作为历史推动者的普罗大众,却沦为过客。
01.序
明仇英《汉宫春晓图》(局部)
大明276年历史中,曾有无数女性,品行奇激,震骇流俗。她们的人生伟丽激越,跌宕起伏,瞬间照耀历史的夜空,正史史家却不屑于记录,于是,她们大都泯灭无闻。
在正史家看来,唯有符合《关雎》、《葛覃》、《桃夭》、《芣苜》标准的“妇德”,所谓至性所存,伦常所系,才有资格纪入《明史•列女传》。他们心目中患难颠沛、杀身殉义之事,不过是明代妇女的血泪史,大多女性灭失自己的人性,穷其一生,总为那一座冰冷的贞节牌坊。即便如此,《明史》自己也承认,“姓名湮灭者,尚不可胜计,存其什一”。
然而大明近三百年历史中,总有一二奇女子,她们出身低贱,蒲门柳质,虽不入正史,却裙钗不让须眉,让那些锦衣纨裦、饫甘餍肥的道学家们,愧则有馀,悔又无益。
这些散落在文士笔记、民间记录中的伟大女性们,有幸留下了只言片语,让后人崇拜仰视。每每读之,无不令人肃然起敬,昊然长叹。今仅举三例,以飨看官,以窥凤毛与麟角。
而她们,绝非历史的过客。
02.蛤 蟆传:刚烈女子的复仇
清·佚名·《纨扇仕女图》
洪武年间,京师金陵。
一位史姓居民,经商出身,家庭小康,新婚妻子也容貌绝美,婚后夫妻恩爱,也算得上美满。
然天有不测风雨。结婚没几年,史某与好友外出经商,途中不慎落水而亡。听闻噩耗,史妻悲痛欲绝。她们尚未有子女,就阴 阳永隔。想是夫妻缘分浅薄,便纵是山盟海誓,更与何人说,数年恩爱,如今却成为孀妇。
按照民间惯例,史妻为亡夫持服三年。期间,那位与亡夫一同经商的好友(失其姓名)非常照顾史妻起居,大概是出于与史某的友谊吧,所谓“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朋友去世,关心朋友家人,也是人之常情。
三年持服结束后,这位好友向史妻提出了婚配的请求。
对大明普通百姓来说,“再醮”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绝非奇耻大辱。生活不是小说,史某去世,生活总要继续。这位好友看起来品行尚可,可以托付终身,于是,史妻答应了他的请求。
再婚后,史妻与后夫算得上相敬如宾,两人连生二子,生活甚是和睦。
然而,一次偶然,却意外地让当年史某去世的真 相大白于世。
一个炎炎夏日,南京城内暴雨倾盆而下,瞬间河海暴涨,庭院满是积水,蛤 蟆也顺水跑到院子里,跳到台阶上。
史妻的一个儿子比较顽皮,拿着一根棍子,不停的将跳到台阶上的蛤 蟆挑落到积水里,如此循环往复。
儿童戏蛤 蟆,听取蛙声一片,好一副夏日雨季图,人间小确幸,也不过如此。
明·佚名·《庭院嬉戏图》
史妻夫妇看到儿子如此顽皮,也未当做一回事。然而,后夫却无意间说道:
“史某死时,亦犹是耳。”
史妻听闻此语,呆在当场,如同劈开两片顶阳骨,倾下一盆冰雪来。
史某当年与后夫同行,溺水而亡,所有人都以为是意外。如今后夫却说史某死时,就如那被反复挑落到水中的蛤 蟆一样!
这其中又是何种缘故?
在史妻的追问之下,后夫终于道出当年实情。
后夫大概觉得两人已婚配多年,连生二子,夫妻本是同根鸟。即使说出实情,史妻也能原谅自己所为。
原来,当年后夫早就贪图史妻美色,与史某同行经商时,故 意以杖将其挑落水中,就像他们的儿子不停的挑落蛤 蟆落水一样。在数次落水后,史某终体力不支,溺水而亡。
史某死后,后夫又故 意接近史妻,求作婚配。未明所以的史妻,竟与杀夫仇人婚配,生活多年,生下二子。
史妻心内掀起无边巨浪。望着朝夕相处的枕边人,便是蛇蝎心肠,不似恁般毒害!
她表面不动声色,心中却有了计划。
第二天,待后夫外出后,史妻狠下心来,痛下杀 手,连杀二子。这个弱女子,以最激烈的方式进行复仇。
然后,她向官府自首,控诉后夫当年杀人之罪。
由于史妻犯下杀人之罪,且杀害亲子,案情重大,需要杖刑、流放。根据《大明律》的规定:
凡祖父母、父母,故杀子孙及家长故杀奴裨图赖人者,杖七十,徒一年半。
杀子虽不至死。但后夫当年犯下故 意杀人重罪,需要抵罪。两案勾连在一起,官府逐层上报,应天府将案件报刑部,刑部拟罪,报皇帝批准。
收到案件奏报后,明太祖朱元璋被史妻的刚烈震惊了。虽是再醮之妻,她得知后夫当年为图自己,杀害前夫,竟作出如此决绝的举动。
最后,朱元璋同意勾决后夫,但对史妻,免于刑罚,且旌异之,将其作为忠烈女子的代表。
所有文献中,此后再无史妻的任何蛛丝马迹。她的晚景大概会比较凄凉吧。在一般人眼中,她或许是个不祥之物,两次结婚,两位夫君均不 得 善终,两个孩子也死于她的刚烈。她可能再无人敢娶。
史妻的行为毕竟过于极端,她为报前夫之仇,将与后夫生下的两个孩子杀害。且史妻乃再醮之身,其身份、行为,不符合程朱理学的教化,实在入不了“至性所存,伦常所系”的范畴。
妇人之德,虽在于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诗书所记,风俗所在,图像丹青,流声竹素。再醮的史妻,怎能入史书,垂后世呢?
于是,《明太祖实录》并未将这个案件写入。《明史》也无她的只言片语。
然而,史妻俶傥非常之行,毕竟跌宕奇崛。当时的所谓“好事者”,为这段往事,专门创作了《虾蟆传》,以褒扬史妻的刚烈,一时天下 流传甚广。
只是多年以后,《虾蟆传》散失。成化年间,这个情节被文士陆容写入了《菽园杂记》,流传于世。
到了晚明时期,一本《欢喜冤家》的小说,根据这个情节进行敷演,创作了第七回《陈之美巧计骗多娇》。
在这部并不出彩的小说中,作者演绎了南直隶徐州的巨万富家陈彩,贪图对河潘璘之妻犹氏美貌,设计谋害潘璘,纳犹氏为妾。潘璘死因却在十 八 年后因蛤 蟆事件意外暴露,犹氏拿着陈彩的诗词报官,将其绳之以法,终为前夫报 仇。
其中的诗词这样写到:
当年一见貌如花,便欲谋伊到我家。
即与潘生糖伴蜜,金银出入锦添花。
双双共往瓜州去,刻刻单怀谋害他。
西关渡口推下水,几棒当头竟似蛙。
最后,作者赞叹,这样的故事“可以惊人,亦足以风世。妙妙。”
只是可惜,史妻以生命与血泪写就的刚烈故事,却沦为三流小说作品中的佐料,让青史尽成灰烬。
可为浩叹!
03.青 楼贞:下九流女子的刚烈
唐寅《王蜀宫伎图轴》
天顺元年正月二十九(1453年2月23日),北京西市口。
南宫复辟的朱祁镇,展开了疯狂的报 复行动。七天前,他刚冤杀了挽狂澜于既倒的于谦,这一天,又一位侯爵勋臣走上断头台。
他的名字叫杨俊,是第三代昌平侯,是正统、成化年间名 扬天下的杨家将成员。按照《国朝献徵录》的记载,杨家本是宋代杨业的后代。父亲杨洪以敢战著名,久镇边关,屡立奇功,声震南北,从百户一直做大将,最后封侯,赐世券,世袭罔替。
非但如此,在杨洪的表率下,长子杨俊、侄子杨能、杨信无不知兵善战,立功疆场。最后 “洪父子兄弟皆佩将印,一门三侯伯。其时称名将者,推杨氏。”大明杨家将的威名,远震殊俗。瓦剌诸部惮之,称为“杨王”。
颖国公杨洪画像
按理说,杨俊长期随父征战,本应功名赫赫。但《明英宗实录》及《明史》的叙事中,这位名将之子极具争议,毁过于誉。他实在是将门犬子,坟头蹦迪,作死小能手:
俊恃父势横恣,尝以私憾杖都指挥陶忠至死。……言官交劾,下狱论斩。……言官劾其跋扈,论斩,锢之狱。……家人告俊盗军储,再论死,输赎还爵。……免死夺爵,命其子珍袭。(《明史•列传第六十一》)
《明史》和《明英宗实录》均记录了杨俊四次严重犯罪,都到了论斩的境地,最后却总能逢凶化吉,顺利逃脱。更为吊诡的是,《明史》还对《明英宗实录》中的记载进行了“净化”。按照《明英宗实录》的记载,这位纨绔子弟实在是禽 兽不如:
并发其尝与父洪争淫 妇,又作歌以扬父丑。狱成,当斩,特命严锢之。……昌平侯杨俊下狱,以家人奏其烝庶母也。……都察院论昌平侯杨俊烝父妾,斩,移审大理寺。俊輙不引伏。……辩俊欲烝未成。狱上,诏曰:俊虽丞庶母,未成,终为败伦伤化,具论如律,严锢之……宥昌平侯杨俊死,削其官闲住。以法司辩其强 奸庶母,罪可疑也。(《明英宗实录》)
综合《明英宗实录》这些零落在各卷的记载,朝堂上不少人要将杨俊塑造成道德败坏、猪狗不如的浪荡子。他与父亲争淫 妇,父亲死后,又烝庶母,最后惨死,实属死有余辜。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
杨俊长期随父镇守北疆,后又独当一面,总督独石、永宁诸处边务,巡回京师周边,保障京畿安全。他的勇猛,绝不次于堂兄弟杨能、杨信。
杨俊有十分突出的缺 陷:飞扬跋扈。他四次论死涉及的罪过,包括贪侈、冒功、横恣、杖死都指挥陶忠、嗜酒、杖打都指挥姚贵、盗军储等罪,莫不与此有关。知子莫若父,杨洪曾向朝廷这样评价杨俊“少失义方之训,长无学问之功。粗率轻躁。”,可谓中肯之论。
即便如此,杨俊仍不失为一员悍将。为何要有人屡次置之于死地?
根本原因是朝堂上不少人要将土木堡之变的黑锅放在了杨洪父子背上,这其中也包括了朱祁镇。
土木堡位于宣府境内,宣府总兵官就是杨洪。在不少朝臣心中,杨洪父子负有直接责任。即使是国之柱石于谦,也曾说过这样的话:
曩自逆虏犯边,俊望风奔溃,将独石、永宁等十一城并弃之,遂使边境萧然,守备荡尽。虏寇往来,如在无人之境,闻者无不痛恨。幸存宣府一城,有洪以守之,虽不救土木之危,以解君父之难,然足以为京师及居庸之应援,接大同等处之声势。(《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五)
按照于谦的逻辑,土木堡之变前,杨俊放弃独石、永宁等十一城,北虏入寇,导致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后,杨洪独守宣府,不行救援。父子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于少保还算比较客气,到了言官那里,杨俊就直接成罪魁祸首了:“都指挥杨俊,捐弃连城,金帛钱谷,动踰万计,墩台不守,烽堠邈绝,致贼乘虚邀留圣驾,臣民荼毒。”
在这种朝堂氛围下,杨洪父子就是再劳苦功高,在改变大明国运的巨大灾难前,也不可避免的被人拿来祭旗。杨洪身居高位,品性端正,无可指摘。于是,骄悍的杨俊首当其冲地成了替罪羊。
《明英宗实录》中的这些指责多少有些泼脏水的成分,实在真假难辨。因此《明史》比较公正地以“阴事”两字,一笔带过。
南宫复辟后,杨洪及承袭的嫡子杨杰都已去世,杨俊因数次犯罪,私德败坏,也被褫夺侯爵,由其子承袭。朱祁镇本就认杨俊为蒙尘北狩的罪魁,此时恰巧有人诬告,说杨俊当年拒英宗入关,英宗回銮,他又指为祸本,于是,朱祁镇借机大开杀戒。
朱祁镇对杨俊的判决是:“俊情罪深重,论法当凌迟处死,姑斩之。其子珍革爵,发广西边卫充军。” 于是,杨俊和另一位“罪臣”范广,同赴西市,即时问斩。
由于是皇帝定案的钦犯,又身负恶名,当杨俊走向西市口的断头台,满腔忠愤无处可申:为国守边,却被诬陷为丢城弃地,身为侯爵贵胄,却被指斥欲烝庶母,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 年。
如今,一同行刑的范广,大概亲朋故旧毕集,呼天抢地的为他送行。而自己竟无一人前来诀别。死前还要遭受这样的侮辱,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杨俊不愧将门之后,仍然表现得极为英勇:
二人赴市,英气不挫。扬又挺身连曰:“陷驾者谁?吾提军救驾者,杀之,天乎?”(《七修类稿》卷五十一)
就在此时,本篇的女主人公勇敢地站了出来。她浑身缟素,翩然而至,向杨俊走来。
她叫高娃,因排行,又称“高三”,是一名京师妓 女,乃下九流之贱籍,自不入史家法眼。
在俗人眼中,她与杨俊不过是娼妇与恩客的关系。然而,这位高娃却与众不同:
京师娼女高三,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杨俊见之属意,因与狎,犹处子也。(《寓圃杂记》卷六)
对于杨俊来说,当年年少轻狂,看到高三美姿容,就见色起意,于是“与之狎”。
然对于高三来说,杨俊却是他生命的全部。这位可怜的女子,大概率因家境贫寒,自幼就被亲人卖入青 楼。但她很可能只是歌舞伎,她对杨俊一见钟情,委身于他时,竟然“犹处子”,仍是处子之身。虽落入青 楼,但她守身如玉,直至遇到意中人,遂以为可以托付终身。
杨俊提裤子走人,大概以为这就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游戏,曾经的桑濮之行,算不得真情。此后数年,他镇守北疆,或许早将高三忘到了九霄云外。然而,高三却做出了更奇崛的举动:
侯去捍北边者数载,高即自誓谢客。(《寓圃杂记》卷六)
在道学家那里,青 楼女子守节是贻笑大方的天方夜谭,确是高三的矢志不渝的承诺: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
当一身缟素的高三突然出现时,杨俊一生的际遇与冤屈,得到了一丝的回响。谁承料想,贵胄侯门,竟无一人送行,桑中之约,却成一诺千金:
杨顾谓曰:“若来何为?”娃曰:“来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观者骇然。(《奇女子传》卷四)
杨俊大概思索片刻,才认出这位女子,竟说出“若来何为?”的话。高三不过是他荒唐岁月中一位烟云过客。大概他从未想过,自他去后,竟有一位青 楼女子为他守节。当他带着满身恶名押赴刑场时,却是这位下九流的女子高呼“天乎!忠良死矣!”。
刑场上那些无情的看客们“骇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还在等着杨俊的人血馒头,却看到了最不可思议的一幕。
这实在与朱夫子的一贯教诲对不上号。一位贱籍女子如何能作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举动?
有了高三的陪伴,杨俊的忠勇之气更加决绝:
杨止之曰:“已矣,无益于我,更累君耳。”娼曰:“我已办矣,公先往,妾随至。”杨挺身呼行刑者曰:“何不快动手。”(《野记•野记三》)
杨俊对高三说:“已矣,无益于我,更累君耳。”,让她不要高呼忠良,这只会连累她。高三却平静的回答,我已安排了所有的后事,公先去,我随后就来陪伴你。
在人生最后时刻,杨俊明白了他得到了一人心,于是不再有任何遗憾,大喊着让刽子手尽快行刑,心满意足地走向了人生终点:
俊已刑,娃恸吮其颈血,尽哀,请淂以针,著其首于颈,袖出帛,自缢死俊之旁。(《罪惟录》)
按照几篇野史的记载,杨俊断头后,高三一边恸哭,一遍用针线将杨俊的断头缝在颈上,并以口吮其不断涌出颈血,莫让英雄血横流。
做完这些后,她从袖中拿出事先准备好 的布帛,自缢于杨俊之旁,毅然决然,同赴黄泉!
这样恐怖片式的场景,却让我们热泪盈眶。
仗义每从屠狗辈,这样的忠肝烈胆之行,竟出自一位青 楼女子。卿死国,我死卿,可矣!
对于这样的忠烈,有人感叹“惜不见其行,又不知其名,何娼之有若人哉!真可谓奇也。”,
高三身居贱籍,自然入不了《明英宗实录》、《明史》这样庙堂正史。朝廷官府表彰节烈忠贞,也断不会覆盖到一位青 楼女子。但她却比那些达官贵胄、士夫儒徒更高尚。
于是,《罪惟录》、《野记》、《寓圃杂记》、《奇女子传》这样的文士笔记,记录了高娃的高行,不容青史尽成灰。
对照着高三的贞烈,再看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君子们,《奇女子传》的作者吴震元发出这样的感慨:
昌平至今不死,高娃亦不死,一时亲戚、故吏,及贤士大夫,无一往者。今何在也,噫!想死矣!
高三忠肝烈胆,她死了,精神却永存;那些贤士大夫今何在,想来坟头草已一人高了吧。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04.护全印:妾室的侠烈
明代《月曼清游图册-闲亭对弈》-陈枚
严格来说,在正史中,第三位女子是留下了些许记录的。只是未记录事实的全貌,让忠义之气埋没太久。
正德六年六月十七日(1511年7月11日),江西瑞州府。
这一天,高安县华林山起义军攻陷了瑞州府城,将这场持续数年的农民起义,推向高 潮:
江西华林山盗陈福一等,攻瑞州府,破之。指挥乐正、通判姜荣、孙宗尧皆遁。(《明武宗实录》卷七十六)
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占领瑞州府城,卫所军溃散,代理知府姜荣等仓皇出逃,全然不顾城内百姓安危,甚至为了自己活命,更置家眷不理:
正德中,荣以瑞州通判摄府事。华林贼起,寇瑞,荣出走。贼入城,执其妻及婢数人。(《明史•列传第 一百八十九》)
按照《万历野获编》的记载,姜荣不能御敌,有着客观原因。他本是工部主事,因京察不及,贬谪瑞州通判,瑞州知府缺位,他暂代知府职,刚到瑞州,就遇到了起义军,仓皇无别,所以无法御敌。
但此人的无 耻,却在于全然不顾满城百姓和自己的家眷,独自弃城而逃。按照大明律法,这样的罪官,应处以重刑。
但不久后朝廷负责纠弹朝臣的言官们,却主动为其开罪。姜荣非但未受到处罚,竟然还因叙功进升五品同知,一时风光无两。
是什么缘由,让这个无 耻之徒因祸得福,加官进爵呢?
很多年以后,人们方才得知,姜荣的荣华富贵,全因其小妾窦妙善之功。
窦妙善是京师人士,姜荣任工部主事时,纳其为妾。从名字可以看出,她很可能是位佛教 徒,妙善是佛教经典中观音菩萨的前世。
明 周文靖 人物图 宝岛故宫博物院藏
姜荣狼狈弃城而逃前,将知府印 章塞给了窦妙善。义军冲进官邸时,窦妙善居别室,急中生智,打开后窗,将府印投到荷花池中。
农民军逮捕了姜荣的全部家眷(包括正妻),准备作为人 质。这时,窦妙善勇敢地站了出来:
衣鲜衣,前曰:“太守统援兵数千,出东门捕尔等,旦夕授首,安得执吾婢?”贼意其夫人也,解前所执数人,独舆妙善出城。(《明史•列传第 一百八十九》)
她处理好了府印,然后盛装鲜衣,出来见义军,说姜太守已率兵出城剿匪,你们早晚会就擒,不要捉拿我的婢女们。
义军看到窦妙善如此华服盛装,又气压全场,俨然主母,判定她是姜荣的正妻,于是,他们释放了其他家眷,仅留窦妙善作为人 质,并用轿子将她抬出城。
就这样,智勇兼备的窦妙善,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姜荣的其他家眷。
在《明史》和其他文士笔记绘声绘色的叙事中,出城后,窦妙善又以自己的智慧,让朝廷印记得到妥善保护:
适所驱隶中,有盛豹者父子被掠,其子叩头乞纵父,贼许之。妙善曰:“是有力,当以舁我,何得遽纵?”贼从之。行数里,妙善视前后无贼,低语豹曰:“我所以留汝者,以太守不知印处,欲借汝告之。今当令汝归,幸语太守,自此前行,遇井即毕命矣。” 呼贼曰:“是人不善舁,可仍纵之,易善舁者。”贼又从之。(《妙香室丛话卷四》)
《妙香室丛话》这段记载几乎与《明史》相同。从记载来看,起义军确实不是匪徒,有最基本的礼义廉耻。瑞州府属吏盛豹父子同时被执,盛豹向义军叩头,乞求他们释放父亲。基于孝义,义军答应了盛豹的请求。
看到此景的窦妙善,敏锐意识到盛豹父慈子孝,是可以信赖之人。她让义军不要释放盛豹父亲,说他们力气大,可以帮忙抬轿子。行数里后,窦妙善看到前后无人,就低声告诉盛豹,让他父子转告姜荣,府印藏身之处。于是,窦妙善又给起义军说,盛豹父亲不会抬轿子,还是放了罢。起义军听从了窦妙善的建议,释放了盛豹父子。
这则记载过于离奇,在《万历野获编》的记载中,窦妙善的言行更加可信,也更能体现她的弥天智勇:
乃又绐贼曰:“可速遣盛父报主人,持多金来赎我,今有盛子作质,不虑逸也。”贼信之。(《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
她告诉义军,可以释放盛豹父亲,让他转告姜荣,多拿赎金来赎自己,反正盛豹在这,不用担心盛父会逃跑。义军果然相信了她的话,释放了盛父。
盛豹父亲获释后,找到了姜荣,告知他府印下落,于是朝廷印记得以保全,姜荣立下大功。后因祸得福,加官进爵。
然而,这位智勇双全、颇具节侠风骨的窦氏,在确保府印安全后,却以最激烈的手段,慷慨就义,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行至花坞遇井,妙善曰:“吾渴不可忍,可汲水置井傍,吾将饮。”贼如其言,妙善至井傍,跳身以入,贼惊救不得而去。(《明史•列传第 一百八十九》)
队伍达到花坞地方,此处原有深井,已得到义军信任的窦妙善,推说自己口渴难忍,让他们汲取井水。趁他们不注意,窦妙善突然跳井自尽。
义军被这样刚烈之行震惊了,他们“惊救”,最后却不得。窦妙善以毅然决然的方式,保全了自己的名节。
按照《明史》的记载,姜荣后来找回了府印,也找回了窦妙善的尸体。七年后,郡县上其事,诏建特祠,赐额“贞烈”。似乎这段忠孝节烈得到了最好 的结果,朝廷建祠纪念,英气长留人间。
然而,正史记载的这段忠烈之气,却远不是故事的全部。正史故 意略去了人性的黑暗。相比于浩然烈气的窦妙善,那位姜荣的表现,实在令人不齿:
姜脱死归郡,才两阅月,复买一姝丽,时议遂大薄之,未几竟褫职去。窦、京师崇文坊人也,都中妇女以淫悍著闻,此女独从容就义,智勇兼备,即史册亦仅见。若姜荣负心,则犬豕不若矣。(《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
窦妙善虽为妾室,却以自己的智勇,拯救了全家,也拯救了姜荣的仕途,侠烈之气,感人肺腑。姜荣倚之加官进爵,本应感恩戴德,铭记于心,至少也要象征性的表现出哀伤与悼念。然而事实却是,仅两个月后,他就把壮烈牺牲的窦妙善抛之脑后,重新购买了一个姝丽作小妾,全无半点留恋。
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卷(宋摹)
他的作为没一点士大夫的廉耻,被骂 “犬豕不若”,也着实不亏。果真负心多是读书人。没过多久,品行恶劣的姜荣,也被罢官褫职。
另一个尴尬的事实是,朝廷虽建祠纪念,但“贞烈”并非谥号,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妾媵身份低人一等,不配得到谥号:
余向见妾媵得谥者而偶遗此,且贞烈祠额,非谥也,然足不朽矣。(《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
窦妙善为这个世界留下一段侠烈肝肠,长传一段忠义奇伟,却因身系妾媵,不是正妻,得不到朝廷的封赠,甚至建祠纪念已属旷典。
然而,她却多少须眉汗颜,又让多少贵妇失色。
05.尾声
明代陈洪绶 《执扇仕女》
大明276年中,多少女子守约以居正,杀身以成仁。她们虽生长环堵之中,却能著美行垂于汗青。
更有多少奇女子,或因身居下九流,难入士夫之目,或因为稻粱谋,未能符合吃人礼教所谓“以懿节自著”。但她们一样蹈忠而践义,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节。
这样的奇女子们,公然被道学家们忽视。她们不入彤管之书,不沾良史之笔,将草木以俱落,与麋鹿而同死。
对于这些道貌岸然的史公们,可以用《红楼梦》开篇概括: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致力于人文领域原创文章。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lzxmw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