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1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住在巴黎有诸多好处,尤其如果你是一个有大把空余时间的影迷的话。巴黎的电影世界相对较小,即使像我这样几乎没有发表过作品、仅仅处于电影界边缘的作家,也能有一些激动人心的经历。一天晚上,我刚从夏乐宫的电影资料馆出来,就被邀请去几个街区外正在拍摄的罗伯特·布列松的电影中当临时演员。
1972年7月初,当我为《电影评论》撰写关于奥逊·威尔斯在好莱坞的第一部作品——最终未完成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的文章时,我得知威尔斯也在巴黎,于是我给他的剪辑工作室Antégor寄了一封信,写了几个简单的问题,结果两天后我接到了他的一位助手打来的电话:「威尔斯先生请问你今天能否和他共进午餐。」

《上海来的女人》
我在地中海餐厅(La Méditerranée)见到了他——这家海鲜餐厅也将在他目前剪辑的电影中占据重要位置——当我开始对他邀请我表示惊讶时,他热情地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没有时间回信。他正在制作的这部电影当时还叫做《骗局》(Hoax),他说这部电影与艺术品伪造师埃米尔·德·霍里以及最近涉及克利福德·欧文和霍华德·休斯的丑闻有关。「这是一部纪录片?」「不,不是纪录片,是一种新的电影,」他回答道,但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
说实话,这听起来有点自卖自夸,不过,就像那天下午他告诉我的其他大部分事情一样,最后都证明了是准确无误的。他本可以说「论文」或「论文电影」,但仔细想想,这一标签几乎和「纪录片」一样不准确,而且容易误导观众,尽管《赝品》既有论文的元素,也有纪录片的元素(还有虚构的元素)。

《赝品》
威尔斯随后的影片《拍摄〈奥赛罗〉》(1978)显然更符合论文的标准,这也是菲利普·洛佩特在他的《全然地,温柔地,悲情地:毕生迷恋电影的论文与评论》(Totally, Tenderly, Tragically: Essays and Criticism from a Lifelong Love Affair with the Movies)一书中对这种形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特别提到自己更喜欢后者的原因,即它有前者无法比拟的真诚性。但《赝品》既是威尔斯最开诚布公的电影,也是他最私密的电影——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着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内涵——因此我们不能用评判其他大多数电影的标准来评判它。
一年多后,即1973年10月15日,我应邀参加了一场私人的预映会,当时这部电影的名字叫《伪作》(Fake)。我被电影历史学家、电影资料馆的长期雇员洛特·艾斯纳叫到了13号俱乐部(Club 13)——一家由克洛德·勒卢什经营、经常用于行业放映的时髦场所。当我大胆地说:「这看起来不太像奥逊·威尔斯的电影」时,她接着说:「这甚至都算不上是一部电影。」但除了威尔斯此前对我说的话之外,我们都不知道其他的背景信息,直到近十年后,他在接受《电影手册》杂志采访时才对比尔·克罗恩说,他刻意回避了任何可能被认为是「典型威尔斯风格」的镜头。

第二年,《国际先驱论坛报》引用了他的话:「在《赝品》(F for Fake)一片中,我说自己是个『假行家』,但我并不是真心这个意思——我不想显得自己高埃米尔一等,所以我强调自己是个魔术师,并称之为假行家,两者不是一回事。我当时基本上就是在伪装。一切都是谎言。没有什么不是假的。」
让事情更复杂的是,影片的制片公司在放映几天后给我寄来了一份资料,上面所写的片名又变成了《问号》(Question Mark),由奥逊·威尔斯和弗朗索瓦·莱兴巴赫共同执导(大概是因为使用了后者的关于伪造艺术品的纪录片的片段),由奥尔加·帕林卡斯(威尔斯的情妇奥雅·柯达的真名)编剧,主要演员是埃米尔·德·霍里和克利福德·欧文(没有威尔斯)。显然,这部「新型电影」给每个人——不仅仅是影评人——都带来了定义和描述上的麻烦。
当片名最后定为《赝品》时(这是柯达提议的——其实,她和巴勃罗·毕加索之间的轶事也是威尔斯编造的),每个人都被弄得昏头转向。我当时在《电影评论》上总结道:「目前,我很满足于称之为《新奥逊·威尔斯电影》,由欧文和德·霍里共同执导、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编剧、霍华德·休斯制片……正如威尔斯在谈到沙特尔大教堂时所说,最重要的是它的存在,而不是建造它的人的名字。」

可以说,我早期对《赝品》的欣赏包括了对它的颠覆性的充分理解(现在也是)。但撇开对艺术世界以及通过「行家」将其商品化的批判不谈——这比《公民凯恩》(1941)中对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批判要激进得多——直到近些年,随着录影带的倒带和停格功能的出现,人们才认识到威尔斯的许多重要技巧是多么的大胆,这使得本片比他的任何其他影片都更适合通过家庭录影带观看。同时,我们也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他在制作这部影片时所采用的方法使他在使用素材时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
对于威尔斯这样一位经常宣称电影艺术倚赖于剪辑的导演来说,《赝品》一定是他最深入的一次努力。多米尼克·维兰曾在1991年出版的《电影剪辑》(Le montage au cinéma)一书中采访过影片的剪辑总监,根据书中的说法,威尔斯的剪辑工作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每周工作七天——只有在米歇尔·勒格朗创作配乐的时间里才会暂停工作——而且需要使用三个独立的剪辑室。

威尔斯在这部影片里「造假」的关键,正如他的其他所有作品一样,是调动观众的想象力,以及让观众因自己的想象力(通常是在不知不觉中)而与这些精巧的设计积极合作——这种无意识或半意识的共谋正是魔术师和演员的倚仗(「魔术师就是演员……扮演着魔术师的角色。」)恰恰是这种默契,让我们能够接受威尔斯扮演柯达的匈牙利祖父,也让我们能够接受柯达在片尾的一场戏里扮演毕加索,当时两人都身着黑衣,在浓雾中穿梭。这一关窍可以从威尔斯在影片中说的第一句话发现——声音最初从黑暗中传来,随后逐渐消失在巴黎车站火车车厢的窗外——这句话既是字面意义上的,也包含了象征层面的意义:「女士们先生们,为了下一个实验,我希望从你们那里借用一下任何一个私人小物件——一把钥匙、一盒火柴、一枚硬币,都行。」
最后,一个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把钥匙。威尔斯迅速把它变成一枚硬币,然后又变回小男孩口袋里的钥匙,与此同时,他还把镜头对准了莱兴巴赫的摄制组,并与他们进行了简短的交流,然后让柯达打开了火车车窗。他总结道:「那把钥匙并没有任何象征意义。」

有人可能会觉得他的观点十分可笑,但我不敢苟同。在接下来的八十多分钟里,这把钥匙从被私人保存,到被拿走,并最终物归原主,恰恰象征着观众在威尔斯的「实验」中所进行的创造性投入和参与。而在这些交互中,无论是对观众还是对威尔斯来说,区分什么是公共的、什么是私人的,都没有听起来那么容易。威尔斯在电影中忍不住炫耀自己情妇的美貌和性感,而此时他还是有妇之夫,这似乎简直是厚颜无耻——尤其是与他在暗示德·霍里的同性恋身份时所表现出的婉转形成鲜明对比,但并不能简单或想当然地指责他仅仅是为了曝露自己的内心和性欲。
在某些方面,他自嘲式的夸夸其谈,比如向刚收拾走一只大龙虾的残壳的服务员点牛排,似乎成了一种面具,而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意图则深深藏在自己的口袋里,就像我们倾注其中的私人想法一样。那些认为各种骗局(包括德·霍里、欧文和威尔斯各自的骗局)肤浅而明显的人,可能忽略了这些骗局的揭露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他各种骗局的实施,其中有些显然既不肤浅也不明显。

关于这一过程的一个直接例子是,当镜头从「一部奥逊·威尔斯电影」向左移动到「与」,然后依次向上移动到「合作」、「某些」和「专家」等词时,我们被要求在胶片盒的侧面拼凑出这一组词的含义,而这些词组与另一个标有「实笺者」(practioners)的盒子并列。由于我们太专注于跟随镜头引导我们的非传统的阅读方向——从右到左,然后从下到上——大多数人可能很容易把「实践者」(practitioners)这个单词读成在字典里根本不存在的「实笺者」(practioners)。
鉴于在这部电影中,「专家」这个词很快就会变得沉重、污浊和双面,我们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的合作者和「实笺者」——威尔斯魔术的观众,他们与威尔斯合作,将魔术付诸实践——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换句话说,我们知道得最多,但其实什么也不了解。
同样,我们也应该仔细观察早期的「看女孩」片段——这可能是影片中剪辑最复杂的一段,尤其是与后期毕加索注视柯达的片段形成了鲜明对比。(顺便提一下,这两个片段使用的配乐都被勒格朗命名为《奥逊主题曲》[Orson’s Theme],不过从威尔斯的安排来看,叫它《奥雅主题曲》[Oja’s Theme]可能更贴切)。如果我们在「看女孩」一段结尾处的适当位置定格,就会发现看似在城市街道上向我们走来的「奥雅·柯达」的几个正面长镜头,实际上并不是柯达本人,而是另一个穿着同样裙子、身材差不多的女人(她的妹妹妮娜)。鉴于整部影片精心设计的「躲猫猫」战术——几乎一直都是支离破碎的马赛克——因此,这两个非常简短的镜头假装揭示了之前许多角度所掩盖的东西,就像那封据称是爱伦·坡被偷走的信一样,可以轻易地在众目睽睽之下骗过我们。

《赝品》之于威尔斯,就如《芬尼根的守灵夜》之于乔伊斯,是一个嬉笑怒骂的公共历史宝库,其中交织着私人笑话和双重含义,并且精心融合了道理和无理,常常让观众/读者不知所云。威尔斯的公共身份和私人身份是如此割离,以至于两者似乎经常出现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甚至不同的大陆上,暴露和隐藏有时就像一枚硬币的反面,而威尔斯想要将自己隐藏在文字中的愿望,在这里反而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自恋。
三年后,当威尔斯制作他那部从未公开的、长达九分钟的《赝品》预告片时,他甚至避免让人说出或看到他的名字(「尽量低调)——除了留下他的摄影师兼部分替身盖瑞·格雷弗提示他「还有十秒钟,奥逊」的镜头。
威尔斯是一位极力避免重复自己的电影人,他力求永远超出观众的期望,从而拒绝任何明显地商品化其导演身份的方式,可以说,他在《赝品》中找到了一种方法,将其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内容与背景联系起来,同时又打破了许多关于作者身份的受人珍视的观念,并戳穿「专家」、「上帝赐予造假者的天赋」等旨在维护这种观念的人和话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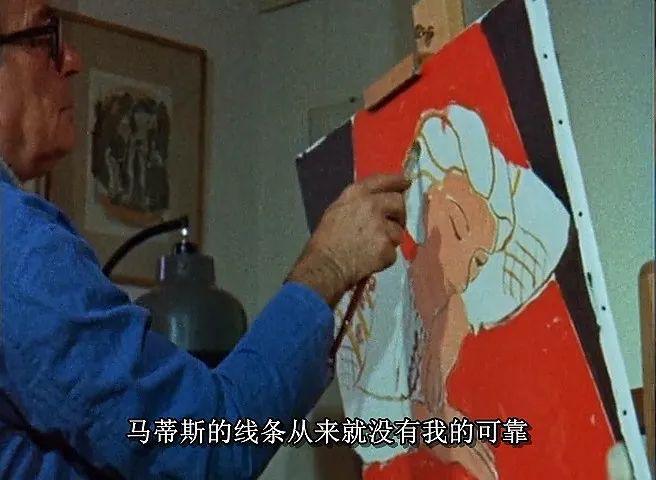
人们经常断言,这部影片是威尔斯对宝琳·凯尔的《凯恩的诞生》(Raising Kane)一文及其关于《公民凯恩》的剧本几乎全部由赫尔曼·J·曼凯维奇撰写的说法(后被推翻)的间接回应。然而,值得补充的是,威尔斯对凯尔的抨击最直接的回应是他高超的半伪造作品《凯恩的反叛》(The Kane Mutiny),这篇论战文章以彼得·博格丹诺维奇的署名刊登在杂志《时尚先生》之上,其中引用了许多威尔斯的话,并对凯尔的文章逐点进行了有力的回应。
密歇根大学教授凯瑟琳·L·贝纳莫在她关于威尔斯的著作中指出,《赝品》中几幅伪造画作的焚烧与烧毁「玫瑰花蕾」雪橇的大火遥相呼应;同时,通过剪辑制造的各种「对话」再现了《伟大的安巴逊》(1942)中关于安巴逊一家所处的社区的人们唠叨的方式;又或者有着吉普赛风格的小提琴、威尔斯的斯拉夫语调以及所有疯狂的飞机跳跃镜头都让人想起《阿卡丁先生》(1955);片中甚至还出现了布谷鸟钟,让人不禁想起《阿卡丁先生》和《第三人》。

尽管有很多遗憾,但这种自我反思正是《赝品》成为威尔斯最可喜可贺的影片的众多因素之一。正如他在远眺沙特尔大教堂时所说的那样——这几乎与我们第一次看到《公民凯恩》里的「仙乐都」的感受如出一辙——「我们的歌声都将沉寂,但这又如何?继续歌唱吧。」
合作邮箱:irisfilm@qq.com
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lzxmw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