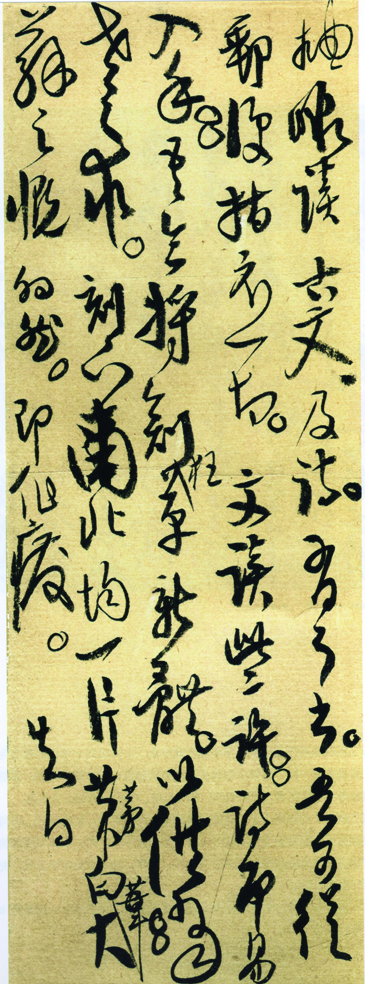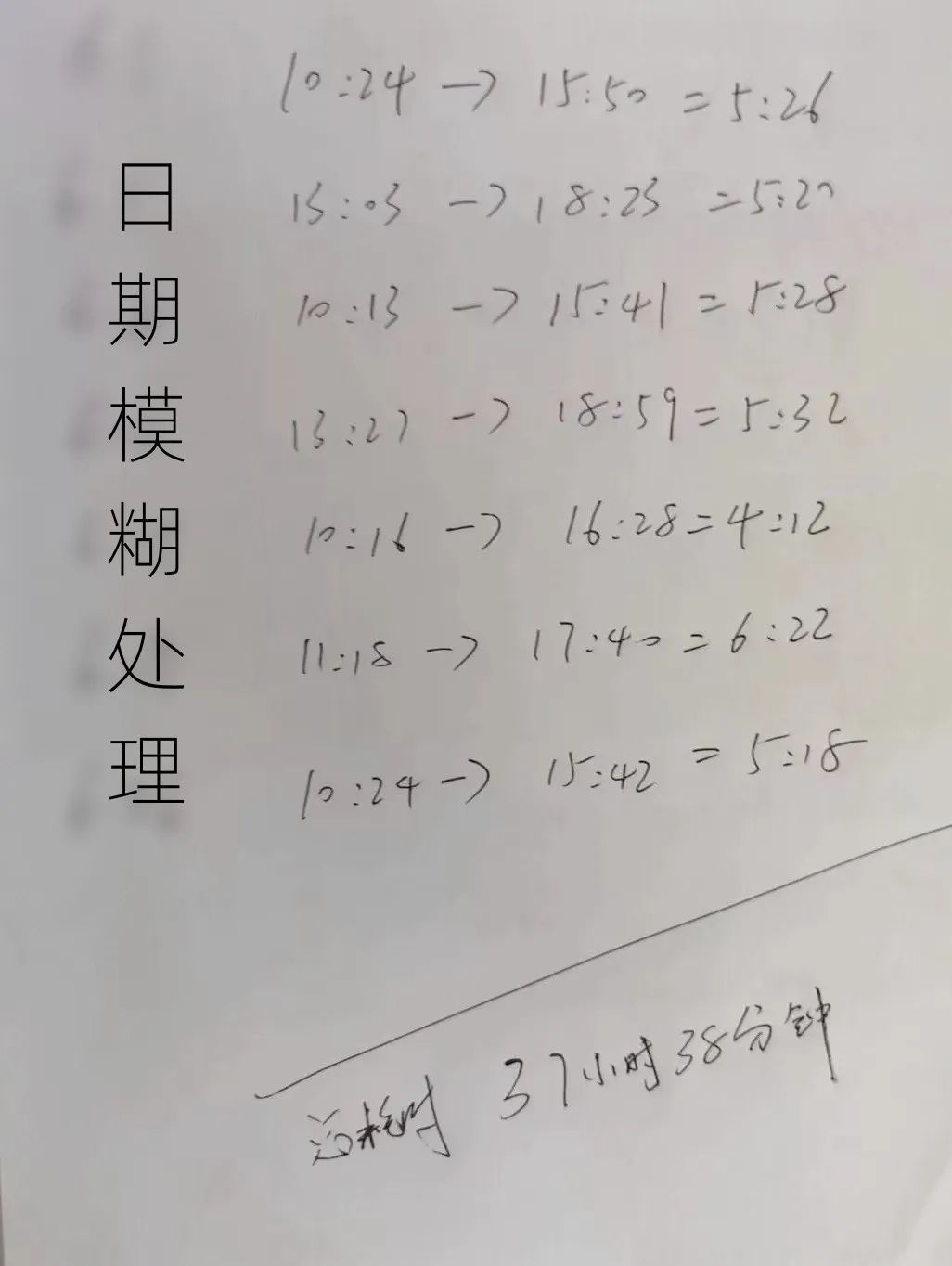酱紫FM出品

值班主播 | 羊城晚报记者 崔文灿
老北京豆汁儿的“难喝”,我是早已有耳闻的。但味道究竟如何,我没尝过。
正巧前段时间出差来北京,闲来时去天坛附近逛逛,碰见一家老牌豆汁儿店。恰逢晚饭时间,心想不如就去体验体验,这被称作“老北京之蜜糖,外地人之砒霜”的豆汁儿,到底是啥味。

店面不大,吃饭的人却不少。我一打量,每个食客都是人手一碗豆汁儿,配上各类老北京小吃,吃得津津有味。排队点餐的食客,也是人人都喊“来碗豆汁儿”。我纳罕:可能这豆汁儿也没那么难喝,不然怎么人人都要呢?
于是,我便也随了大流,要了一碗豆汁,一个芝麻烧饼,一个焦圈。取餐处,切成细丝的腌萝卜条堆在铝盆里,供食客自取。我也仿其他人的样子,夹了一小碟。
那舀豆汁儿的服务员麻利地从大锅里舀出一碗灰糟糟的液体,放在托盘上。看起来,倒也像平时喝的黑芝麻豆浆。但一入口,一股酸馊味直入口腔——活脱脱就是“加热了的泔水”!

我悄悄问身边打扫卫生的服务员:“你们的豆汁儿是不是过期了?”她哈哈一笑:“喝不惯这味儿是不是?豆汁儿就这个味儿,绿豆发酵后做的。老北京人可不觉得酸!”
听人说,豆汁儿越喝越香。我努力品着,极力想从那酸馊之味中尝出哪怕一小点的清甜,可惜未果。我咬牙喝下几口,也不好被周边人瞧见那副囧相。眼瞅着身边食客那哧溜喝豆汁儿的快活劲儿,怎么也想不明白,都是一口锅里舀出来的豆汁儿,这些人怎么吃得这样欢喜?他们有的把炸的酥脆的焦圈泡在豆汁儿里——就像把油条泡进豆浆,把油饼泡进鱼头汁里那样——再加几口咸菜丝,不亦乐乎;有的单喝豆汁儿,再就着旁边碟子里的芝麻烧饼,好像也是有滋有味。而我呢?芝麻烧饼、焦圈和咸菜倒是被自己吃得一干二净,唯独这碗豆汁儿,就像一块烫手山芋般,无从下口!我草草抹了下嘴,像被打败的士兵,落荒而逃。
香港导演胡金铨先生曾说:不能喝豆汁儿的人,算不得真正的北平人。这话,现在看来有几分道理。即便是我这个离北京三小时车程的北方人也喝不惯,想必南方人来喝,也得喝的龇牙咧嘴,苦不堪言。
我不知道北京人为何养成这样的口味,但我却知道,从前不分贫穷阔绰,不分男女老少,豆汁儿是老北京人人都喝的,而且喝得上瘾,称之为“本命食”。当年东安市场的小店“豆汁何”,名声一点不小于隔壁的大饭庄东来顺,常常有穿着华贵、坐着私家轿车的达官贵人,专程来喝五分钱一碗的豆汁儿。《燕都小食品杂咏》中说:“糟粕居然可作粥,老浆风味论稀稠。无论男女齐来坐,适口酸盐各一瓯。”并说,“得味在酸咸之外,食者自知,可谓精妙绝伦。”相传连京剧大师梅兰芳,也是豆汁儿的“铁粉”——他隐居上海时,他的弟子去上海演出,每每都以四斤大玻璃瓶灌满豆汁儿坐飞机带给师傅飨之。
看来,我也是无缘“得味在酸咸之外”,只能静静做个看客,看人饮其味,品那精妙绝伦之口感了吧!

来源| 羊城晚报
文字 | 羊城晚报记者 崔文灿
图片 | 视觉中国
编辑 | 大方、Hanna(实习)
校对 | 谢杨柳
审签 | 鲁钇山
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lzxmw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