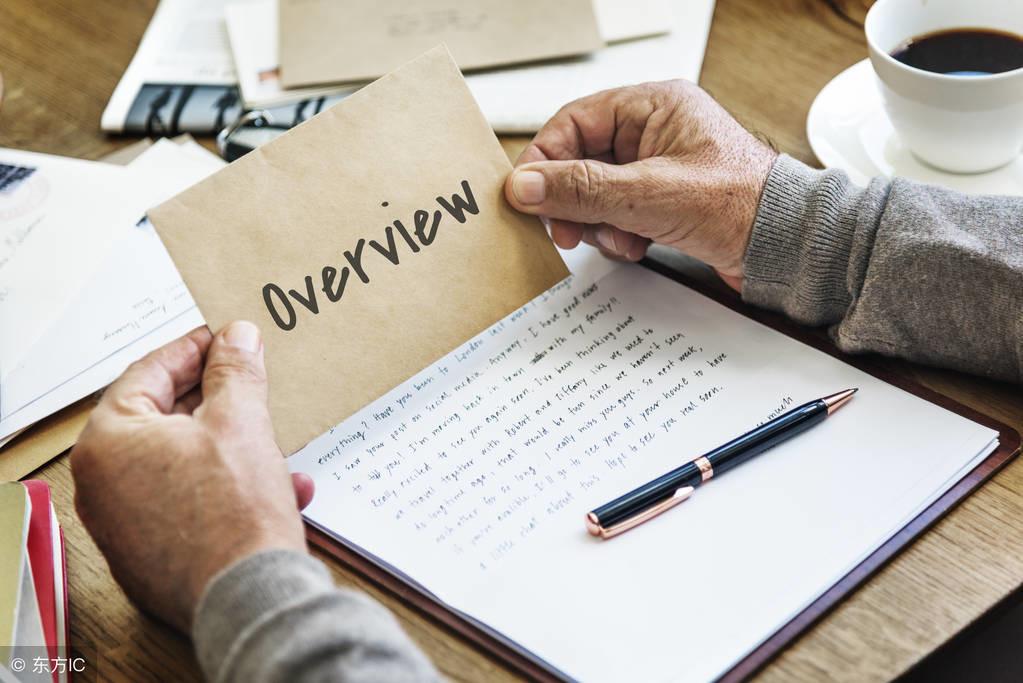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大秦赋》讲述了秦始皇嬴政在吕不韦、李斯、王翦等人的辅佐下扫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故事。
两千多年来,在我国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短暂的王朝使得人们具有如此恒久的兴趣去关注它。那么,为何完成统一大业的,不是别国,偏偏是山东六国公认为“天下之仇雠”(《史记·苏秦列传》)的秦国呢?不是别人,偏偏是被认为“行桀纣之道”(《说苑·至公篇》)的秦王嬴政呢?在《大秦帝国》(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一书中,作者萧然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在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完备礼乐制度的中原齐鲁诸国看来,世代隅居于关西的秦国,不啻化外之区、野蛮之邦,因而曾长期置之视野之外。落后是痛苦的,因落后又受到排挤、轻视,更是加倍的痛苦。《吕氏春秋·不苟》记有秦穆公训诫大夫公孙枝越职行事说的一段话:由于“秦国僻陋戎夷”,即使事事、人人都照制度办事,“犹惧为诸侯笑”,可你为什么还要那样做呢?备受屈辱而又极不甘心于屈辱地位的内心痛苦,溢于言表。但秦国的这种地位,到战国初期也还没有根本改变。当山东六强,甚至包括若干小国,都不断在这里那里会盟角逐较量的时候,已具有相当实力的秦国,却还是被冷落在关西。
当时年轻气盛的秦孝公在即位祭祖时,痛哭哀告说:耻辱啊耻辱,诸侯如此卑视我秦国,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耻辱呢?出生于寄居地赵国、因而原名赵政的秦始皇,母亲是歌舞伎,父亲虽是秦国王孙却作为人质羁留在赵国,加上秦、赵常常作为敌国相互攻战,因而他的整个童年时代不仅与通常王子王孙都能够享有的优渥生活与良好教育无缘,有时连基本的温饱和人身安全都很难保障。每当为躲避赵国搜捕,不得不鹑衣百结地露宿在邯郸的僻里陋巷时,他所关切的绝不是未来如何去吞并六国,而只能是眼前如何填饱辘辘饥肠!
秦国和秦始皇所以能成为中华第一帝国的创造者,先哲和时贤已作出多种探究,原因很多。如地理条件的优越:东据崤山、函谷之固,西拥雍州膏腴之地,不仅物产丰饶,且攻守皆利。又如秦内政较为严正,士大夫比周结党之事相对较少,百官恭俭敦敬,勤于执事。再如秦民勇悍善斗,秦地音乐诗歌都有一种犷野意味。特别是商鞅变法后,坚持以军功封爵,将士更勇于公战,犯白刃,蹈汤池,一往无前。秦国还长期以厚禄高位吸纳各国“客卿”,使许多在本国得不到重用的智能之士纷纷西游,以求在秦国一展抱负才华。此外,也许还是最主要的,就是统一已成为时代要求,统一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但详尽地按照这些“条条杠杠”为这个古老的帝国写出一部带有总结路数的文字,也许会使人索然寡味。如果说大秦帝国因暴亡而不免使人有流星之叹的话,那么它的兴起却决非一蹴而就,它那短暂而辉煌的光焰,是经由漫长的历史阶段积聚而成的。因而如果我们要寻访帝国之魂,就不能不追溯秦人的整个奋斗史:从一个遭受迁徙的民族,到附庸——诸侯——王国,直到成为天下共主的大秦帝国。

当然,胜利有胜利的来由,失败有失败的原因,历史最终归结为必然。战国七雄中的其他六国又是因何而亡的呢?
司马光是生活于11世纪的著名史学家,他在《资治通鉴·秦纪二》中作了这样评论:“从(通‘纵’)横之说,虽反复百端,然大要合从者六国之利也。昔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飨宴以相乐,会盟以相结者,无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国也。向使六国能以信义相亲,则秦虽强暴,安得亡之哉!夫三晋者,齐楚之藩蔽;齐楚者,三晋之根柢,形势相资,表里相依。故以三晋而攻齐楚,自绝其根柢也;以齐楚而攻三晋,自掘其藩蔽也。”
六国若能以信义相亲,即使秦国再强大,也不会灭亡。这是司马光的中心论点。文中追溯了历史,认为先王分建列国的宗旨,就是为了诸侯间相交、相乐、相结,共同保护国家。可是六国却偏偏违反了先王的宗旨,不是自撤藩蔽,就是自绝根柢,致使秦国有机可乘而遂行其志。
与司马光大致生活于同一时代的苏洵写过一篇专论六国之亡的名文《六国论》,文章一开头就点出了全文要旨:“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
所谓“赂”,指列国割让土地,贿赂秦国,求得苟安。文章接着算了这样一笔账:“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也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
就六国之亡而言,赂地也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原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弱国若以赂地予强国求得自保,必然导致敌我强弱之势以反比例的形式迅速向前发展,结果只能是加速自己灭亡。
第三家是苏辙,即苏洵之子,苏轼之弟。他同以《六国论》为题成篇,其着重做在一个“势”字上。与苏洵的一开篇就揭示全篇要旨不同,他却是从容道来,层递设问:何以有“五倍之地、十倍之众”的六国,反而会败亡于秦呢?然后就势托出一句道:“不知天下之势也!”

三家文章都力透纸背,经他们犀利的笔触一剔发,赂秦一类策略的危害便洞若观火。那么是否当时六国的决策层都那么低能,连割地赂秦,只能使秦国愈强、自己愈弱这样一些道理都一点不懂呢?恐怕还不至于。春秋战国是我们民族智能大昂扬的时代,中原六国都有自己第一流的智囊团。这里确实有一个智能问题,但首要的却不是智能问题。再高的智慧,有时却会受拘于眼前一点实际利益而变得苍白无力。列国因何要赂秦?苏洵文章中有一句话:为求“一夕安寝”。就因了这“一夕安寝”使他们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得了近视症:既看不到“天下之势”,也看不到“日削月割,以趋于亡”即将降临的必然结果,从而采取了这类饮鸩止渴的慢性自杀对策。
那么六国君主又为什么大都会患这种近视症呢?这恐怕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所得。苏洵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历史上,开国君主,或中兴君主,特别在他们创业之时,都是有胆有识,能够面对艰难困苦而坚毅不拔、发愤有为,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性格优势和人格力量。具有这种性格优势和人格力量的人,才敢于“暴霜露,斩荆棘”。而坐享其成的君主就大多不是这样,一旦进入没落时期,多数王室成员更是沉溺在无休止的感官享受之中。他们根本不知道艰苦创业为何物,因而一旦战祸临头,首先想到的决不会是如何去迎战,而只能是如何去逃避这场战祸。既然人家喜欢土地,那就“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地割吧,只要它能换到“一夕安寝”又何乐而不为哉!
杜牧《阿房宫赋》的结语是闪烁着历史真理光辉的名句:“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所以,秦王嬴政吞并六国的大决战,既是实力、智力的一次大较量,也是人性、人格的一次大搏杀。
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lzxmw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