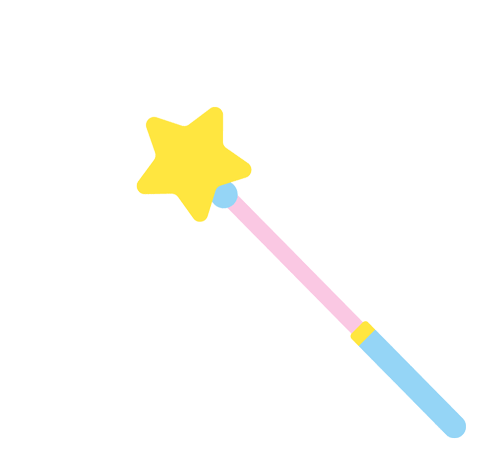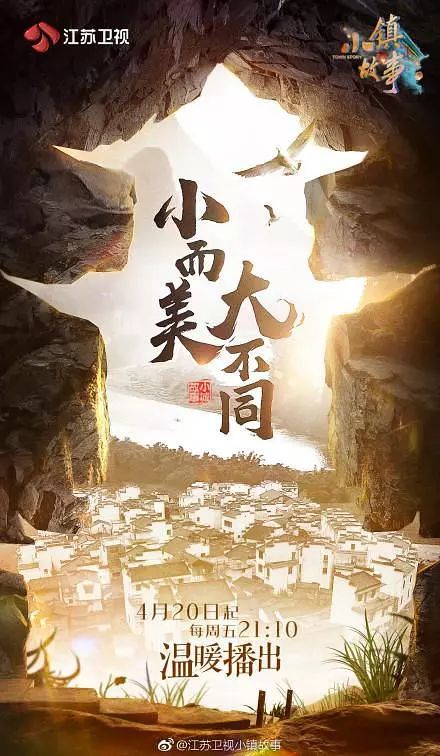引
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
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有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宋玉《对楚王问》
如今,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早已无人传唱,但下里巴人在楚国脍炙人口却是毫无疑问的。楚灭巴后,巴人成为楚客,《巴人》由此从古代巴国传进中原文化。时至今日,川东、鄂西等地仍保留着“巴”的称呼。谁也说不准“巴”是怎样得名的,只知道“巴”是古代西南独具特点的一个土著民族。
春秋时代,巴国由于夹在秦国和楚国两大强国中间艰难的生存,由于巴蜀两国不但有珍贵的食盐资源,而且物产丰富,所以不断的被秦楚两国觊觎蚕食,国土面积不断缩小,直到战国中期被秦国彻底吞并。就这样,拥有先进的文明随着巴国的突然消失,十几万巴国人竟也不知所踪,千百年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谜团。那么,神秘的巴人今何在?
篡夺母系社会获得的巴人壮大
最早的巴国是由五个氏族部落联合形成一个大型的部落集团,其中巴人以武力和船技上的优势,获得了集团的领导权,巴人首领称廪君。随着大部族繁荣昌盛起来了,困难也随之而了:山洞不够住,野兽和植物也不够吃。于是,廪君带领全部族寻找到更广阔、更富饶的生活。
廪君盐水河遇盐水女神,盐水女神对其一见钟情,于是软语温存,真诚挽留。入夜,盐神来到廪君船上,与之共宿;天明,则化为荧荧飞虫,麇集万千同类,昏天蔽日,使廪君莫辨东西。为了挣脱盐水女神的温柔乡,廪君差人将一缕青色丝线作为定情之物赠给盐神,要她系在身上。随后的白日,廪君照着青丝一箭射去正中盐神。只听得微微地一声呻吟,空中仿佛有一道亮光一闪,盐水女神怀着满腔的哀怨和凄苦,缓缓地坠落,随波涛东去渐渐地沉入了水中,于是天地于是豁然开朗……
神话如此,却并不是没有根据。这段凄美的爱情映射到现实中,盐水女神的身份应该是人而非神,所谓的“神”应指对神的祭祀权,拥有此权者当被视为神的宠儿和神权之拥有者。盐神部落为母权制社会应是没有疑问的,廪君的得势,即已表明男权的出现和母系社会走到了尽头,权力颠覆已成为必然趋势。
事实上,随着男性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日益强大的他们需要以财产与实力来重新划定社会地位,不再满足于狭窄的生存空间、贫瘠的生活与不合时宜的女权统治。浪漫而极富悲剧性的强故事,爱和温情乃至抗争都无法遏制男性对权力的欲望,最终的胜利者强夺了母系部族的神权,而巴人也就过渡到更利于发展的父权社会,他们辗转迁入恩施,他们的后辈成为了如今的土家族。
一个女人担负起的土司盛世
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唐崖镇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内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坟墓,墓前立有石碑和石牌坊。碑面中刻“明显妣诰封武略将军覃太夫人田氏之墓”,后题“皇明崇祯岁庚午季夏吉旦立”。在墓前有一较矮小的素面石牌坊,造形简单无雕饰花纹,牌坊以石建成,牌坊两侧以鼓形石护柱,上以石为坊,凿榫相接。这就是田氏夫人墓。
如果说土司覃鼎的军功是由功德牌坊来彰显的,那么田氏夫人的故事则是通过世代子民的口碑相传的。当年唐崖覃氏土司与龙潭田氏土司之间常年为了争夺地盘而兵戎相见,为了平息战乱,龙潭土司提出“和亲”之策,于是龙潭土司的女儿田氏与唐崖土司之子覃鼎结为夫妇,土司之间的战争也因此偃旗息鼓。土家族“皇权”世袭到18代覃鼎手里时达到鼎盛,明朝天启年间,覃鼎率兵先后奉命征讨重庆地区,皆胜利而归,其妻田氏也被诰封武略将军零夫人。此时,覃鼎实际统治着鄂西南、渝东几千平方公里的地盘,位列恩施土司之首。
覃鼎去世,其子宗尧即位,颇行不道,开明的田氏夫人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胸襟,以女流之身担负起了唐崖土司的统治。她专门派人在成都等地学习当地汉人养猪、种桑、养蚕、刺绣等技术,回来后传授给当地百姓土民。田氏在土司内务管理上,绳以礼法,“内则地方安谧,外则转输无乏”。后来,田氏将王位传给了覃鼎的侄子覃宗禹,这是唐崖土司史上子袭父位的一个例外,它反映了田氏的远见卓识。
幸存至今的唐崖土司皇城,见证了土家族悠久灿烂历史文化之缩影,这座皇城遗址镌刻着鄂西延续400多年的土司制度的兴衰,凝聚着土家人高超精绝的建筑雕刻艺术,隐蕴着鄂西土家人元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活,储存着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信息。
而我,更坚信这是一段不渝爱情的见证,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走进这座风雨沧桑的遗址,残垣四处林立,石路纵横交错,苔藓肆意疯长,宛如一幅年代久远的风情画。曾经带领千千万万的鄂西土家人的土司城,却掩映在青草丛中,已然破败不堪。只有那一座牌坊,在夕阳里昭示着土司曾有的繁华和辉煌。
一路迁徙,走进诗人笔下的世外桃源
“君不见太白人中仙,谪仙于此曾盘旋。又不见涪翁千载士,居黔访旧亦游此。”如明代诗人黄溥在《客星山》中描述的一样,仙居恩施自古便是文采汇聚之地。唐宋时代的大诗人大词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寇准、苏东坡、黄庭坚、陆游等,都在恩施留下了足迹,也留下了不少传世的诗作。
巴人的恩施,地处武陵山腹地,其西北还有大娄山东延的齐岳山,东北有大巴山的一部和巫山。诗人们来到或经过恩施,总免不了跋山涉水,面前常常不是险峻的高山就是幽深的河谷。王维有《晓行巴峡》诗:“睛江一女浣,朝日众禽鸣。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登高万井出,眺回二流鸣。人作殊方语,鹦为旧国声。”看到恩施的船上的街市,树杪上的桥梁,以及人们说话的奇特的方言,让诗人的旅途劳顿立消,代之而起的是惊奇、欣喜。白居易有《入峡次巴东》诗:“巫山暮足沾花雨,楚水春多逆浪风。两岸红旗数声鼓,使君楼艓上巴东。”诗人春天乘船初到巴东,看到高峻的巫山,湍急的江水,还有绵绵春雨中的五色的山花,心里感到无比的喜悦,这是恩施的奇妙的山水给予远离故园的诗人的慰藉。
巴人后裔,如今恩施的大山儿女
据推测,巴国在覆灭之后,巴人大规模迁徙,而他们建设的家园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记载的桃花源一模一样。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的猜测,桃花源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桃花源里躲避秦国战乱,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可能就是巴人。
大巴山深处的土家族,复杂的地形地貌决定了民居建筑依山傍水、依势而建,被俗称为“吊脚楼”,独特的民居建筑更加显示了民族风情,其承载着土家人的智慧,在这四面环山之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也是一种宁静安逸的享受吧。
土家族爱美,土家族的妇女大多都擅长刺绣。脚上的绣花鞋,绣花鞋垫,身穿的花边衣,腰系花围裙,还包括枕头、门帘、床巾上面花纹图案都是经过心灵手巧的土家族姑娘一针一线绣出来的。巴人舞是土家族传统的舞蹈,巴人舞刻画了土家人的平时生产生活状态,如狩猎舞表现狩猎活动和摹拟生活姿态。土家人缅怀祖先、追忆民族迁徙艰辛、再现田园生活就会跳起巴人舞,蕴含着土家族的文化元素是土家族人民千百年来创造的精神财富。
我觉得,我好似在这里找到了消失千百年的下里巴人,然而,他们又那样欢快而热烈的摧毁我的成见。于是,在恩施的我,在巴人故里的我,在土家族家园的我,想起那首诺源的诗:
他们也许并不知道那条路还有多长
他们只是在作暗暗计较,让时间在无声的掌纹里泅渡
那粗糙的皱纹,在被火光猜透的夜晚
如同渐渐剥离的漫途,不得不把离群索居的人群
交给一场坚韧的行走
任何貌似真知灼见的反抗都将对他们立判生死
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lzxmw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