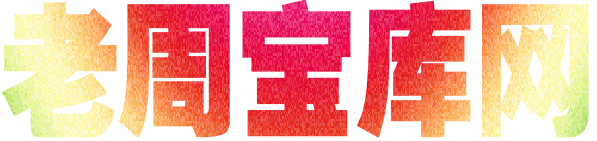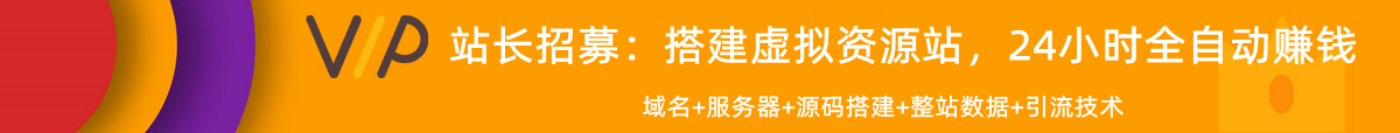盲妃/璇央
(图片源自网络)
本文刊载于《飞·魔幻》杂志2016年7A
一
素缟加身不过半月,衔月便接到了赦封公主的圣旨。侍女鱼贯而入为她换上锦衣金冠时,她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抗拒。自她丧夫之后,面上便只剩冷漠这一种神情,只有在她的父亲桑蠲登基那日,她才在人前展露了几分笑意。于是侍女们在私下里议论,都说公主怕是已经傻了。
能成为金枝玉叶那是许多女子都艳羡的福气,可桑衔月并不是个好命的女子,她被封公主那年正是双十年华,如今却已成了孀妇,她的丈夫是前朝太子,死后谥号敬章。
很多年后史书会记载,敬章太子萧诩,庆元二十七年春谋逆,兵败自杀。可在朝代更易之初萧诩尸骨未寒之时,真相还没有被重重时光彻底掩埋,敬章太子真正的死因仍有部分人清楚——他是死于大将军,即新帝桑蠲之手。
早在前朝,那时的帝王就已是桑蠲手中的傀儡,许多人都在猜大将军会在什么时候没了耐心给天子送上一樽鸩酒后自立,毕竟君弱臣悍的局面天下人都看得分明。然而随着太子年岁渐长,这样的局面却渐渐被打破。萧诩少年早慧文武兼备,十三岁领将印,数立边功。
许多人都说,若太子登基,必为一代英主,岂容外臣觊觎国祚。
早些年,桑蠲与萧诩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和睦,甚至为了安抚桑蠲,萧诩娶了桑蠲最小的女儿桑衔月为正妃。可惜翁婿之间到头来终免不了相斗,萧诩输在了年少,没能逃过兵败身死的结局。他死后,桑蠲一手掌握了朝政兵权,不到半月的时间里便逼着梁帝禅位,将其封做了安乐侯,自己则登上了皇位,改国号为郑。
眨眼间王朝更迭,被夹在萧诩及桑蠲之间的女子少有人在意,她的父亲杀掉了她的丈夫又如何,区区女子的悲喜左右不了这天下大势。只是那些自认为是她亲近之人的人难免会对她生出几分怜悯。当衔月身边的侍女第五次在她面前欲言又止,第四次想方设法引她去散心,第三次委婉含蓄地提醒她节哀时,她终于明白了这些人是怕她太难过。
新的王朝建立时正值暮春,她伏在窗棂上,恰有落花轻盈地擦过她的眼。她猛地颤了颤睫,像是在压抑忽然涌起的泪,但实际上她并没有什么泪可流,侧颜清冷,在秋阳下有如冰雪雕成。“你会为了一朵落英而难过吗?”她发问,语带讥诮。
二
萧诩曾是衔月的丈夫。一开始,衔月就知道萧诩不喜欢她,在她还没有做他妻子时就知道。
衔月能够记起与萧诩的初识,在十二岁那年的除夕,她第一次有资格随父兄入宫赴宴。彼时,她年纪尚幼,宫内的一切于她而言都是新奇。
那年萧诩年十四,却已出任羽林中郎将,执掌禁卫。衔月在家中只是个并不受重视的女儿,那时觉得自己可以跟父亲一同入宫,是她莫大的荣耀,欢喜得彻夜辗转难眠。
次日进宫,她见识到了什么是天家奢华,皇宫的殿堂华贵炫目,宫墙高大像是巍峨山川。下车后,十二岁的孩子在宫娥的彩衣罗衫中花了眼,一晃神便离开了父兄走上了一条岔道。
起初,她并不知畏惧,满怀新奇,一边走一边赏着夹道花木。渐渐地,她越走越远,忘了来时的道路。正惊惶时,忽瞥见重重梨花之后似有行人,她心中一喜,忙分拂花枝急急上前,一抹孤冷如雪的身影就那样突然又温柔地落入了她的眼底。
园林中最古老的梨树下有锦衫少年负手而立。那日起了很大的风,他的衣袂与落英一同翩然,听见动响后他扭头,正对上衔月的眼眸。
在见到这个少年之前,衔月从没在任何一个人的眸中看到过那样深的茫然,他眼中藏着的是一片无尽的雪原——十二岁的衔月目光锐利毒辣,一眼便看穿了少年所有的寂与哀。
“你是谁?”这句话她脱口问出。
少年歪着头打量她,带着警惕,并不说话,他生了十分好看的眉目,却不愿显露半分笑颜。
衔月猛然意识到了这是皇宫,自己是个外来客,于是清清嗓子,道:“我是大将军的女儿。”
下一刻,衔月便被对方的目光吓了一跳,她清楚地从这个年纪相仿的少年的脸上看到了杀意,虽然只有一瞬,可还是让她心惊。她吓得后退了半步,还未想明白自己是怎么惹恼了他,便见这人阴沉着脸扭头离去。她下意识地伸手扯住他的衣袖,怕这人走了自己找不到路。
少年没有回头,衔月听见了他开口,很清晰的一个字,“滚”。这是她的夫婿萧诩此生对她说过的第一句话。
三
在收到父亲赐婚的旨意时,玉琼殿的侍女们颇有几分受宠若惊。新帝才登基,正值诸事繁忙,衔月作为一个从来就不受喜爱的女儿,竟能让帝王在百忙中抽空理会她的婚事,实在让许多人都意外。
但于衔月而言,这是意料之中。即将成为她夫婿的是帝都世代簪缨的名门之裔,谢氏的第三郎谢澴。谢氏素来懂得见风使舵,从前攀附萧诩,而今桑蠲得了天下,他们便主动求赐婚,算是有眼力见。
衔月自该面圣谢恩,侍女匆匆为她换上华服。玉琼殿位于皇城西北,是衔月从东宫迁出来后的居所,略有些偏僻。
侍女搀扶着衔月上车时犹欢喜得喋喋不休:“谢郎君是帝都出了名的俊美人物,公主这回可以放心出嫁,陛下为公主寻这一桩亲事,可见是看重公主。呀,公主小心脚下……唉,公主这双眼,陛下想必也会设法寻医的。”
衔月伸手按了按眼角,挤出一丝平和的笑,她道:“都八年了,早就习惯了。”
衔月的眼,盲于十二岁那年。十二岁时的衔月还只是个懵懂的女儿家,久居闺中不知朝局。那年她随父入宫赴宴,遇上了一场兵乱,朝中与她父亲争权多时的一个宗室意图刺杀她的父亲。宫中的宴席往往通宵达旦,酒酣时许多醉酒的人被带到后殿休息,她跟随母亲一同去照顾醉了的父兄,后来不知不觉伏案睡下,醒来时映入她眼底的,是盛大的红莲。
有人想要她父兄的命,在后殿纵火,所幸她的父兄虽狼狈却四肢俱全地逃了出来,否则哪里还会有后来的皇图霸业,可母亲和她很不幸,一个死在了火中,一个被熏瞎了双眼。
后来,梁帝为了安抚臣子将那名宗室斩首,她的父亲也就息事宁人了。再后来,她才明白那时想杀她父兄的人其实是梁帝,那个被推出去的宗室,其实只是个无辜的替罪品。
庆元十九年的那场变故在彼此心照不宣下被揭过,母亲的命、衔月的眼,再没有人提起。
反倒是梁帝在后来萧诩大婚时借酒感慨了一句,盲目皇后,自古从未有之。
事实上她也最终没能当成皇后,萧诩死了,而她即将成为谢家妇。真不知那时梁帝是已然料到梁朝将在他手里结束,还是纯粹因他儿子娶了一个盲女而心有不甘?衔月不得而知。
衔月记得十五岁出嫁时的情形,记得那时的惶恐不安,陷入一片黑暗中的自己是怎样战战兢兢地被牵引着,走过重重阙门后被交到一个冰冷的手上。那些旁观者的窃窃私语,无孔不入地钻入她的耳中,或是嘲讽,或是哀叹怜悯。
没有人告诉她该怎样做一个妻子,更没有人告诉她,怎样做太子的正妃。
那个牵着她手的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她在喜乐震天中忽然记起了十二岁梨花树下清冷的身影,记忆里的少年容颜端秀,可眼眸中藏着冰与剑。她心中愈发惶恐。
礼成之后,她在等待中迷迷糊糊睡下。后来他推门进来时,她被猝然惊醒——十二岁的大火之后,她再也没能安然入眠,任何风吹草动都使她警惕万分。
“是我。”她听见有个略哑的少年嗓音,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接着脚步声迫近,她慌得一把拔下了簪子攥在手中。
可等了许久也没有感受到有谁触碰,她太过紧张以至于没有听出细微的窸窣声,是萧诩睡在了地上。那时的衔月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后来她才反应过来,其实不只是她防备着萧诩,萧诩也防备着她。
四
路上,衔月被人拦住了去路。那是衔月的熟人,从前梁帝最信任的宦官。
“安乐侯想见公主。”他说。
安乐侯便是梁帝禅位后的封爵。
“不见。”衔月没有犹豫地回绝。
“公主果真不去见一面吗?安乐侯想与公主说一些,太子昔日之事。”
衔月看不清说话人的神情,但她听得出昔日里跋扈无比的阉党首领而今的凄凉。风悄然而过,风中隐隐晋代杂着笛声清冷。自从萧诩死后,衔月便再不曾听人吹笛,可眼下的笛曲,带着几分熟悉。
“这离別枝殿很近吗?”她笑问。
“是啊,很近了。”宦官答,又不死心地道,“既然都到这了,公主不妨见一见……”
別枝殿是安乐侯被软禁的地方,这位亡国的昏君曾在诗赋与音律上堪称一绝。方才吹笛的人是他。衔月想起来了,在东宫的某个夜晚,萧诩曾无意间说起,他的父亲在他儿时手把手教他吹笛,所以难怪他们父子吹出的曲子,是那样相像。
衔月冷冷一甩车帘,坐回了车中。御者扬起了马鞭,宦官尖利的哀求被甩下。
可走了很远,那笛乐都仿佛追在她耳畔,她伸手摸了摸眼角,一片干燥。这笛声太熟了……
衔月与萧诩大婚之后,萧诩便待她如路人,每晚就寝时也从不与她同床,他总是睡在外间,与她隔着一幕珠帘。
十五岁的衔月知道自己在被嫁入深宫的那一日起就不该有闺怨,枕衾冰冷时她也没什么可抱怨的,能和萧诩相安无事地过完一生,已是她最大的心愿。
只是她那时常莫名坠入噩梦之中,梦里她回到了十二岁那年的火场,烈焰朝她逼近,将她吞噬,而她无处可逃,四周都是绝望。她常被吓醒,然后彻夜辗转难眠。
有一夜,她却听到了笛声。她一直觉得笛是风流清灵的乐器,可那夜的笛声十分悠缓平和,有一种近乎幽静的清冷,似寒夜白梅悄然而绽,美得让人心惊且静得使人叹息。
她听得出是谁在吹笛,她想,原来他也没有睡着啊。她不开口,就那样静静地听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她不知道萧诩那夜吹的是一支什么曲子,后来她又听到了许多次萧诩在半夜吹起这支曲子,每每听见,她便会心中稍安。她忘了心中的畏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点点退散的,也不记得是哪夜她试着开口同他说:“很好听。”
笛声停住,她紧张得屏住呼吸。但很久后她听见他说:“我父亲教我的。”
她知道萧诩与梁帝的父子情深厚,虽是帝王家,可他那样轻易且亲切地说“我父亲”,衔月不禁生了几分羡慕。“我父亲从来不会教我这个……”她讷讷道。
“那你父亲教你什么?”出乎意料,他接了话。
“我父亲……并不喜欢我。”衔月嗫嚅道。
“为什么?”他的声音从黑暗中、珠帘后传来,并不近,也不遥远。
“父亲常年征战不顾家,只有兄长们做了什么出色的事他才会笑一笑。我是个女孩,不知能做什么让他喜欢。”
“那你母亲呢?”
“母亲啊,她很温柔,很慈爱……”可惜她已经死了。这后半句话她没有说出口,将话岔开,“你母亲呢……”大约是在半梦半醒的缘故,对他的生疏也淡了很多。
“我母亲端庄雍容,很多人都敬重她。她在我十岁那年病逝了,她生前常教我儒家经籍,她走了很多年后,都还有人赞她是贤后……”他声音温柔,明明还是衔月熟悉的音色,却仿佛换了个人在和她说话。
萧诩,其实也是个很温柔的人。她在迷迷糊糊睡下时忽然意识到了这点。
之后很长的时间里,萧诩和她依旧不会说话,可夜里他们会交谈,对于那段光阴,衔月能记住的是夜的幽静和他悠缓如溪水的叙述。衔月有时会想,如若岁月能这样一直平静下去就好了。
如若能……就好了。
父亲将她嫁给萧诩时从来没有想过让自己的女儿就此安宁康乐地携良人共度一生,他是有野心的人,衔月知道的。嫁给萧诩一年后,衔月挑了个日子归宁,在父亲阴沉的话语间,她明白了自己要做的究竟是什么。
五
谢恩不久后衔月接到了谢澴的邀约。约在帝都郊外的一处园林,名义是赏花。可衔月一个看不见的人有什么花可赏,说到底,不过是有婚约的男女在婚前的一次探底罢了。
“公主要去吗?”侍女问。
“为什么不。”衔月接过邀帖摩挲着,“说起来我与谢公子可是故人呢。”
“故人?”
衔月不再开口。她的确见过谢澴,曾经谢澴的身份,是萧诩帐下的参军。而她曾在萧诩的营帐中待过。
萧诩文武双全,梁帝便刻意用这个儿子来收回握在权臣手中的虎符。萧诩十三岁那年便开始在羽林中任职,十六岁掌禁军。十八岁那年,梁帝将他调去北疆御敌,为的是让儿子在军中树立声望。萧诩这一去不知几时能归,他走之前衔月去了梁帝那请求同往。
梁帝素来是个没主意的,那日多饮了几杯酒,听衔月言辞恳切,便答应了。然而萧诩不许她跟着。“北地苦寒,有什么好去的。”
“殿下是妾的夫君。”她固执道。
他扭头看着她,道:“桑衔月,你不用在我身上费心,你我是怎样的关系,彼此心知肚明。你无非是要接近我,然后为你父亲图谋。”
他面无表情地说完那番话,转身离去再未回头。几日后,萧诩离开东宫远行,果真没有带上她。衔月也不急,从父亲那借了护卫十余人,一路去追赶萧诩。
那时世道并不太平,路上流寇甚多,衔月匆匆出发时带上的随从都是好手,可也还是免不了遇险。其实若干年后再回忆旧事,已感觉不到太多的凶险,那时她只是在混战中与她的护卫走散,偏偏她是个盲人。
她跌跌撞撞地行走于山峦之间,荆棘芒草划破了衣衫肌肤,却没有多痛的感受,她只是害怕,出于一个盲人对世界的恐惧。后来她缩进了一个狭小的石穴中熬过了一夜,做了一夜的噩梦。
她没有想到的是,后来第一个找到她的人,竟是萧诩。
隔了经年的岁月,衔月已记不清太多当时的细节,她能想起的,是一个颤抖且炽热的拥抱。
她几乎不敢相信那人是萧诩。
她以为她会听到讥讽、斥责,可是都没有,萧诩只是用力地抱住她,很久后才说:“衔月,如果你死了,我会难过一世。”
桑衔月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可萧诩告诉她,她死了,他会难过。
不可否认,这句话和萧诩怀抱的温度触动到了她,所以在那一瞬,她忽然忘了她已经知道的真相,忘了自己的恨。那个父亲亲口告诉她的,关于她眼盲的真相。
六
“公主知道吗,八年前害公主眼盲之人,是萧诩。”游冶之时,谢澴忽然道。
衔月挑眉不语,轻嗅一朵折的栀子花。
“八年前公主及陛下一行在入宫赴宴时遇刺。而那时带兵火烧后殿致公主眼盲的,正是敬章太子。”谢澴一面说着一面觑着衔月的面色。他谈起这些,无非是想试探衔月心中是否还有萧诩罢了。
她宛转低笑,道:“早就知道了。”
她嫁给萧诩没多久,一次归宁,父亲便将这个真相告诉了她,目的是断了她爱上萧诩的念头。
然而因为萧诩的那个拥抱,衔月对他终究没能恨起来。之后她跟随萧诩在北疆待了下来,她仍深居府邸,一切仿佛与在东宫时没什么两样。可有很多都不一样了。比如说萧诩回来时常带伤,她能嗅到或深或浅的血腥味。
这是战场上留下的伤,北地并不太平,即便贵为太子,也有死在这儿的可能。
她在某日忍不住问:“何苦?”
他生来是皇子,本该锦衣玉食,享尽荣华。
说这话时她正摸索着为他上药,他的气息近在咫尺,她听见他说:“哀哉黎元。”
“殿下不为自己而活吗?”她忍不住抬首问道。
他似乎笑了一下,道:“衔月,你难道为自己活过吗?”
衔月默然。他们一样,却又不一样。萧诩活着是为了君父与苍生,桑衔月是为父兄野心而活,却是为了自己能更好地活下去。她姓桑,别无选择。
七
在北疆的那段时日,衔月和萧诩一点点地熟稔起来。这在计划之中,意料之外。
衔月渐渐地也知道,萧诩原来并非冷情之人,知道他也会笑,知道他也会窘迫。闲暇时,他会陪他论诗、品茶,恍若友人。直到后来胡人大举来袭,北疆岌岌可危。
萧诩向帝都求援,可帝都的公卿耽于美酒,援军迟迟不至。
衔月看着萧诩每日愁眉紧锁,忍不住提议:“殿下或许可以向我兄长求救。”她兄长手握强兵。
“他不会来的。”萧诩摇头。
衔月无话辩驳。的确,她的父兄盼着萧诩去死,就算萧诩不死,能折损他手中的兵力也是好的。
“不如由你出面劝说?”他提议。
“我……父兄素来不心疼我,我去只怕无济于事。”
“算是为我一搏吧。”他坚持道。
于是衔月终究还是被送出了城,踏上了南下的路。
走之前她问萧诩:“能送我吗?”
他说好。
她又指着自己的眼,道:“我看不见,你能在送我的时候吹一支曲子吗?”
他也说好。
离开北疆时,衔月果真听到了萧诩站在城楼上为她吹的曲。那是衔月最后一次听萧诩吹笛,那也是衔月生平听过的最凄切的一支曲。
八
“公主,安乐侯病危。”衔月听见侍女清晰地说出这句话,“他想见您。”
“病危?”这两字的音在她舌尖滑过古怪的调,她想要冷笑,可终究没能笑出声。毕竟,安乐侯是那人的父亲呐。她想到这,自以为如铁的心一点点柔软,她不愿承认自己的不忍,可她终究是不忍的。
“罢了……去见见他。”她说。
安乐侯从来都是享受帝王的荣华的,可他临死时的凄凉,让人唏嘘不已。
“你来了。”垂死的老人在病榻上睁开一线眼。衔月没说话。
“听说,你要再嫁?”
“是。”她答。
“世上怎有你这般寡廉鲜耻的妇人。”回光返照中的老人愤恨地用手指着她,“我儿那般地信任你,可你害死了他还能在他尸骨未寒时另嫁。”
衔月深吸口气,无神的眼眸一片平静:“他死,是因为你。”
北疆那一战,最后还是胜了,自此之后萧诩在军中威望愈盛。桑家父子忌惮于他,一面施压逼梁帝将其召回帝都,一面设下种种陷阱离间梁帝父子,终使萧诩起兵逼宫,而后被那时是大将军的桑蠲以替帝王诛逆子为借口名正言顺地杀死了。也就是说,如果梁帝不猜忌自己的儿子,萧诩原本是不用死的。
老人狰狞冷笑道:“你有负我儿,还要否认什么!”继而咬牙切齿,“我知道你恨诩儿,可你一个女子有什么仇怨不惜杀夫,不过是所谓的盲目之仇,杀母之恨罢了。”
许多人都叹息,说萧诩败于年少,败于不能隐忍,少有人知道,萧诩会败,是因为他的妻子背叛了他。衔月十二岁那年眼盲,却并非全然失明,只要对着强光,她便能辨认出模糊的景物。在所有人都没有防备的时候,她泄露了萧诩的布军图。衔月不语,任昔日高贵无双的帝王在垂死时状如疯癫般怒骂。
“可昔日害了你的人根本不是诩儿!”这句话被恨恨吐出,如石破天惊。
“那年我密谋刺杀你前来赴宴的父兄,可就在最后关头竟为你父兄所知晓。他们为了脱险,便在后殿放了一把火,正是这把火,毁了你的眸子夺了你母亲的命!可叹这一切都起源于一场拿不上台面的阴谋,我连辩驳都做不到。”
衔月不觉将手抚上了眼眸,道:“也就是说,他其实无辜?”
“自然。”老人瞪着衔月,“只是诩儿自幼心仁,只因当初提议刺杀你父兄的人是他,所以他一直对你心怀愧疚,所以他娶了你。呵,你也不想想,桑家不止你一个女儿,他为何娶你这个看不见的!应该愧疚的人是你才对!我虽快死了,也要将这一切告知于你,我倒要看看你如何能坦然嫁入谢家!”
难怪,难怪萧诩从匪盗手上找到她时会那样紧张,难怪他对一直对她爱却不敢爱。
“这样啊……你该早些说的。”她眼角滑落一滴泪。
原来萧诩不欠她的,萧诩任何人的都不欠。原来他们本该有机会更早一些举案齐眉。可叹,那些时光都被他们错过了,等到她蓦然发现她对他的恨都只是一场笑话时,他已入了坟墓。
原来,这便是所谓的缘错。
“阿诩,我们太迟了。”
九
桑蠲称帝后的第二个月,公主衔月风光大嫁。冬末之时,她早产生下了一个婴孩。
相比公主出嫁及诞子的喜讯,前代帝王的死便显得太过寂寞。安乐侯病亡后以侯礼草草下葬,萧氏满门绝后,此后他陵前再无香烛。
谢家小公子满月时落了一场大雪,桑衔月眯起眼努力地去看雪,竟依稀捕捉到了萧诩的影子。
记得在北疆,战场中他也是一身银铠,身上的血迹就如簇簇朱梅。
庆元二十六年时,衔月并不知道如果一个人几次三番地将她的命看得比自己的命更重要,她该不该感动,该不该爱上那人。但在那一年,当衔月在寻找兄长搬兵的路上意识到了萧诩其实是想用这个方法使她离开北疆逃到安全的地方时,她毅然返回了北疆。当然,萧诩支开她或许并不是因为他爱她,也许是出于同情,也许是出于道义,但衔月就是没法独自离开北疆。
“愚蠢!”萧诩见到逃回来的她时,气急败坏地骂道。
她含泪莞尔,道:“愿与殿下共进退。”
萧诩怔住,而后用力地将她搂进怀中。
守城之战打了足足三月,极为艰苦,可唯有在那段时光里衔月能忘了她姓桑,萧诩也不再是太子而是一名普通的边将。因为不知道死亡什么时候会降临,所以每一刻的携手都弥足珍贵。后来萧诩胜了,得胜那日,衔月却从他身上看到了浓重的忧虑。
“这一仗我胜了,可日后我不知我是否还能胜。”他说。
衔月明白他的意思,她握住了他的手,也是希望他懂她的意思。她与他共进退。
然而萧诩却说:“衔月,我并不想赢。”
“为什么?”
他似是笑了,在她额上落下一吻,道:“傻丫头,若你这双眼能看见,若你能走出闺阁,你就会明白,这是一个怎样的世道。帝王昏庸,朝堂腐朽,你知道吗,我的母亲之所以病亡,是因她规劝父亲励精图治无果,才郁郁而终。如果我不姓萧,我希望明君取代昏君,有人能站出来破旧立新。”
“可你是梁国的太子。”
“要么,等梁国传到我手上时由我来清除积弊;要么,我与这肮脏的世道一同湮灭。”衔月记得他是这样答她的。
后来他起兵逼宫,兵败自杀,无论如何,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结局。
在他起兵前的那夜,衔月拽住他的衣袖哭求:“不要死,不论胜负,都不要死……”
他手指轻轻掠过她的鬓角,想了想递给她一个卷轴:“我猜我父亲之所以会对我猜疑,是受你父兄离间。他们才是幕后的主谋,如果我兵败,他们势必得势,你好好把握时机,若眼见着我败局无可逆转,就将这个交给你父亲。”
那是一份萧诩亲自画的布军图,若是将这个交给桑蠲,不论有没有用,都在向桑蠲表明她其实是倒向自己父亲的。
“我不——”
“听话。”他掰开她的手指,将卷轴塞进她的掌心,“桑衔月,你忘了吗,我们可是仇家啊,不要太在意我……”
她死死地抱住他,嚎啕大哭。
“我答应你。”最后他被她缠得只能苦笑,“我会回来的。”他在他们俩的手腕上分别系了一根红绳,笑说,“听老人的故事说,绑着这个,下辈子就还能做夫妻。”
那时她因悲伤而浑浑噩噩,等她明白萧诩那些话是什么含义时,她已经失去了他。
萧诩说来世还做夫妻,是因为他清楚,一旦败了,他们今生缘便就此尽了,即便他想活下来,桑氏父子也不会准许。后来她差人打听到了萧诩死时的情形,回话的宦官说,他并非自杀而亡,是她的父兄将他勒杀。他答应过她要活下去,他尽力了。
那宦官还说,萧诩倒下时最后一个动作,是轻吻系着红绳的手腕。
冬日雪霁后,衔月感受到了阳光浅浅的暖,她轻摇着摇篮,才出世不久的孩子在笑。
御医说这个孩子生来体弱,这是意料之中。她曾在身孕不足一月时驾车马穿行两军阵营只为泄露军机,那时萧诩已经没有赢的机会了,她将他亲手递给她的卷轴交到她父亲手中,是为了在萧诩兵败后给自己还有孩子谋一条出路。
她在怀有一个月身孕时压抑丧夫之恸,好像从未在意过那个曾是她丈夫的人。她在怀有两个月身孕时隐瞒了这孩子的存在嫁入了谢家。她战战兢兢十月,终于诞下了这个孩子。流着萧诩的血脉,是萧诩存在于世最好的证明,也是他们曾彼此防备、试探、熟悉、相恋所留下的唯一痕迹。
一切都将被抹灭不容存在,但至少,还有这个孩子活了下来。她在冬阳中小心翼翼地抱起小小的婴孩,轻轻吻了一下腕上的红绳,一滴泪悄然从眼眶中滑落。
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lzxmw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