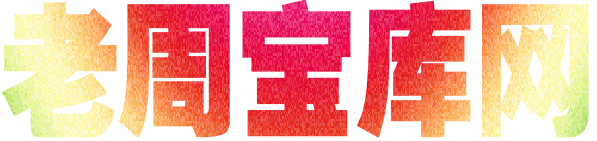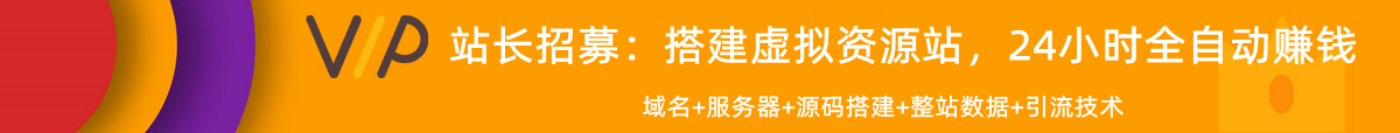七仙女下凡.曝光 110cmX140cm 2014
四、下午
下午没休班去了老宅子看门,因为想一个人待着。骑了一路没碰见人,戴口罩成了政令下的自律。
院子里麻雀喜鹊鸽子照旧喳喳咔咔咕咕在窗外,凑成一团,成双成对,忽来忽去。画室里的画儿都是需要继续画的,脑子却被七仙女占着,就抽出来,摆在那儿,无从下手。在手机上翻看物流信息,知道从日本寄来的画儿已经到了青岛,猜想可能在取货时出现的弯弯道道。冲了壶普洱,稀释一下这一晚加一早的粘稠,回味那几天的平淡。翻看那些天长长短短的笔记,不由得跟自己打趣儿:人家猪八戒喜欢肥腻,是因为投错了胎,本来是神仙;我们牛家先人有谁位列仙班?有,外国亲戚艾萨克.牛顿,据说就是在疫情期间被点名候补的;咱也试试,不写“十日谈”,把今年生日前这一百来天写完,说不准能留下点东西。
考中了博学鸿词科的我,要在巨笔擘画的时代洪流旁镌刻出一股涓涓细流,用浸透了柔情的琴弓在恢弘交响的乐章中牵扯出一缕婉转的旋律。业余画画空余写作的我,不会拉、不会叫、也不会钻刻雕,而且不认为艺术“高”于生活,它只是个人思想生活的剪影。剪辑现实的剪刀可以给裁缝,可以给医生,可以给疯子,都可能出彩,但绝对不能塞给个装疯卖傻的骗子。每天口口声声为了自由世界,按住经纬线撕扯撮合,“尘归尘,土归土,主的归主……”边念叨边飞针走线,说是要演一出《图兰朵》,实际是不想让别人参与编程的血腥玛丽闯关。还冲着镜头歇斯底里:“你们就是被寡人吓唬住的一群傻怂,哭吧,翻白眼儿吧,胡言乱语地祈祷吧!大小便失禁?让自由女神来擦、来拭、来揩、来抹,‘敲吧,门终究会开的!’――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所谓精彩的人生,在西方是指与时、空签的契约足够多,签字的笔换得足够频繁,在东边就比较麻烦,捧着秤砣叼着秤杆,准星准不准还得孟婆判定。死了,那边在天梯下查看一下旅行箱就行。这边,奈何桥头,老婆婆闭眼朝你身上摸擞一把,一拨收下秤砣以做川资,一拨绕上秤砣踹进河里,称杆儿都搉折烧火煮了茶汤。
我执着于“七仙女下凡”的魔幻现实主义,妄图用方程式推导出画面表白出风格,图示观念倾吐淤积,掉进了虚脱的反映论里。以为批判就是逆流而上,就是中流砥柱,参照物只是目力所及的回旋的当代日历。迷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繁花似锦总在精耕细作之后,没注意时令,只顾及了锦的僵硬,习惯性地调节变量合并同类项,没去理会等式两端昭示的均衡与印证,妄费了这个时代指数级增长的G,可惜了这个红尘净土间可以剖析自我、把握证悟的时机。
我所在这两通院子,解放前的主人是张七,是他抗战初期继承父亲老张的遗产。快解放时,他从上海到香港定居,上岸时来接的本茨一字排开就是七辆,昭示他就是那个著名的七公子。“土改”时,他以给父亲在祖坟旁立个衣冠家为由短暂回归,据说保住了军队占用的上院、学校使用的下院名义上的所有权。人民公社兴起,他在大公报上宣布与粤剧明星的妻子离婚并将个人资产放弃,回到老家重新落户时形单影只。文化大革命中,以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家的走狗和孝子贤孙身份被斗挨批。七七年过了年,在为了修路要拆的大队分给的张家祠堂的东厢房里,写澄清历史请予平反的材料,同宗的小学生张小小对他说:“七爷爷,你在干么?你的作业怎么这么多?俺能不能钻你家的地洞玩儿?俺几个从荷花池子那儿钻过来过!”
正在为自己的胡拉闲扯加标点符号,俺媳妇来电话:“听你中午说得那么诡异,想去新房看看,不行别装了,还那么高,卖了算了”。我说不是有答案了吗?没有鬼,只有异。“等会儿我回去,陪你走着去?”
给门卫出示了通行证,跟值班人员说领着媳妇来看看新房,也就测了体温沿着路灯到三号楼西单元坐电梯上去。我告诉她,这楼的首层是0层,没有13层,咱的15楼西没减也没增。她没有回应,紧抓着我的手像是在那儿仔细听。出了电梯,推了推楼梯间的门问怎么锁着?我说是没住人地反映。看到百十平方的面积上工具材料散放着,她说“是,不可能跳舞,地方也不够。”“不对吧?如果是两个人,床那么大就行。”“又你瞎说。我是说这房子的格局小!”为了说服,我领她上了阁楼,打开北边的天窗,嘟囔着阁楼对于退休后的我不小的意义,拉她上了木工梯,俯视这龟缩着的小半座城,遥望昏沉天光下的海平面,以她年近半百的年纪。
“哎――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
“你是说活的头儿还是盼的头儿?”
“我是说疫情。”
“是啊,活着就过去喽,等呗。”
“我是说这么个情况下,什么也不敢想,什么也不敢干,憋死人。”
“是吗?我认为啊,咱们平常所说的自由,是对时间、空间的个人掌控,忽略了人的存在是自我意识的存在,是针对参照系的存在……”
隔壁电梯间嗡嗡了一阵后咔哒一声,应该是到0或-1层接人。
“因此,自由意志才是自由的本质,所以,别太把外在的环境当回事儿。”自认给出了答案,可脑子还在往下钻。伴着电梯提升的嗡嗡声,默默申诉:“对吗?不清楚环境,怎么确认自己?不理解自己的欲求与舍弃,自由意志从何谈起?”答案含混在电梯的咯噔一声里:“康德:自由即自律”。
“你不去给12楼解释一下?”俺媳妇一问,吓了我一跳,“啊?噢。你看谁捉到过鬼?”
“就这么算了?”
“算了吧,谁心里没有鬼?揪出来怕是还认得。”
“你在说么?我看你心里有鬼!”
“走,去看看?”
灯火通明的大街空空荡荡,一个街角非常像爱德华.霍珀画的酒廊,本来琐碎的细节被色块井然有序地收纳,晃动的树影,模特静止的橱窗,嗖嗖响的几根电线贯穿在墨蓝色的天上。一只猫从垃圾桶旁窜出,甩开几声狗叫,钻进广告灯箱下的窄缝。一个遛狗的人被活蹦乱跳的狗牵着闯过红灯,在人行道上忽左忽右。店门被风鼓动发出“欢迎光临Welcome”的招呼声,空间在时间中艰难地喘息。
“摘了口罩,咱俩跑回去?”
“快走,别摘。诶,12楼的电话。慢点。”
“邻居,你好。”
“你好,你好,现在方便接电话?”
“方便,您说,就是风大,你可能听不清。”
“哦,刚才我听到你们上楼了,叫了外卖我在等,麻烦您啦。矫局长已经给我回复,谢谢你啊!”
“不用,不用。都不容易,听矫局说你是过来做生意。”
“湖北的,和金总是老乡,咱们见过,吃饭时店里有事我先走了。当时你说要买金总的餐桌,我说就买黑胡桃的,他说还谁喜欢你哪鸭子的颜色?”
“哦,我喜欢。”
“鸭子?”
“木头。”
“噢――”
“也就,你让金总给了你我的号码?”
“是,但是,我没说那事。”
“金总哪时候了还没睡?”
“是他打来的电话,说院子里的狗总叫,找我聊聊,你住我楼上这才知道。”
“噢,他没被隔离?”
“他想回去回不去。我是正月初三离开家初四晚上到的,领导说从初五算二十解套。”
“这就到了。”
“是,也快‘五一’了,那几间门面的租子也就到了期,怎么交?没生意。”
“不是有政策吗?”
“你是说政府的建议?没人听,都不松口。政府街的那个房东听我一说就开始又噘又骂,我把电话挂了微信发了,给了我一支花,蔫了的。”
“等等吧,看怎么落实。”
“矫局长说的也是。”
“他爱吃。”
“鸭子?”
“嗯。”
“年前我已把库存清零,那东西不能放,放了发梗,皮紧,还不压秤。就等年后老婆提了现货,不成想我们那里也开始封城。就这么贴着钱干瞪眼。哎――对了,我那儿有块黑胡桃大板,你拿去。”
“没到那种地步吧?”
“有面子也不在块板上,重要的在用上。”
“是。只是我那儿没多大。”
“你那儿不是在装修吗?小王总干的?还能差?让木匠裁裁就行。”
“好好的东西别瞎弄。想想前阵子的好光景,养精蓄锐,然后大赚一通。”
“是啊,买卖不靠卖,靠赚。可这连卖的机会都不给,就是个穷命。满打满算买了个12楼东,却落了个13不靠。我靠,解除隔离也在13号,星期五,好歹都是自找?”
“您的意思――昨晚。”
“魔鬼撒旦!”
“啊?”
“打了你们的电话都没用,就下了楼,整栋楼都是黑的,仔细听,什么也听不清,大风。感觉地下室有光,看不清,就把着栅栏往里望,看见一个女的特别漂亮,还有早上领你进去的那个女的,在陪着一个小孩玩,还有几条狗,还有一些服务员。”
“跳舞?”
“窗帘堵着,看不清其他屋。冻得我赶紧往回跑,回到家,还能感觉到像打夯一样的低音炮。手机照着上到你家天窗,发现东头有亮。抓着铁筋爬过去,我去,你猜怎么着?一帮美女穿着长筒袜戴着手套口罩,瞎拍瞎照乱蹦乱跳,几个男的光着膀子套着隔离服,在里面乱摩乱蹭瞎弹瞎敲。不敢拍,怕有闪光灯。风啊雪啊地伤了风。”
“嘿!疯狂派对。”
“不对!撒旦和12女巫――魔鬼夜会!早上检查的来量体温,不高!中午就开始哆嗦打喷嚏发烧,明天怕是就要被抓着了!”
“别胡说,是排察检测。烧到多少?”
“38度多,不高。就请您替我跟矫局长聊聊,还有几天也就罢了?”
“想不去?这事儿――他可不敢应承。”
“那我就让检测的给您打电话,你把情况说给他们听听。”
“怎么说?”
“就说我去你家阁楼上看,风大,天冷。”
“你这是――来来回回多少趟地着凉、受惊?你说,我听,我说,谁听?谁也说不清,说了也只当耳旁风!”
“我说的也是实情。先是上下了一大通,没找着动静,后来索性一探究竟。看了他家的客厅餐厅,我就想弄清还有什么我没有看到的隐情,也就玩了命地上下……”
“好啦好啦!等着核酸检测吧。这也是为你本人负责,看看到底有病没病。”
“那医院里到处都是……”
“谁说的?起码比咱这儿清静!穿着隔离服进进出出,想感染也难。何况不用再叫外卖,管饱还干净。”
“不――行吗?给他们看我录的他们都哪样儿了――也不行?”
“不是行不行的问题,而是这跟你发烧没关系的问题!”
“关系?什么关系?关系什么?关系你们的关系!如果不是录的太烂,我早把它发个挨家挨户。那么多人从哪弄的N95、隔离服?老百姓嘴上这块尿布,不防进只防出……”
“好……好,我是没招了。你找矫局说,好不好?”
“说――还说什么?”
“嗯――撒旦――你就留着。”
“这――呵呵呵,都是我的错?我早应该想到你们就是一伙儿的!。”
“谁、谁?你疯了!”
“矫局长让我不要跟你提上帝。金哥说千万不要不舍得东西。店一定要维持下去,出过那事后店名已改过一次,这次我要是进去,那可真就是下了地狱,老婆孩子也一起。”
“大家都是想帮你!测了,得了,咱就治,测了,没事,万事大吉。生命重要还是生意重要?”
“你们才重要!你们的命才重要,你们的关系才重要。”
“胡闹。你――”
“我只是感冒!你们才应该挨个开刀、化疗!你,牛老师,先补补钙,再――然后,矫局长直接下猛药,楼上的排好队ICU报到,楼下这就切掉。那么长一桌子美酒佳肴,一头一尾装地是那门子妖?煞有介事点着蜡烛,守护?超度?死了凉了还没入土!眉来眼去,平分?贼眉鼠眼,独吞?图得不就是这口老头子的棺材本?涂脂抹粉,坦胸露乳,孝服能哪么穿?丢人现眼。死人不张嘴就能吃饭,用不着这么多人伺候使唤,摆弄人的是钱!狐媚魇道,狼狈为奸。那几个小子在阁楼上狂欢,就不怕他爹的阴魂不散?这传染那传染玩哪个不传染?败家子儿,下三烂。多好的姑娘,爹娘给了个贱样?能讨个好吃好喝还是打赏点赞?哎!你咋不画下来――最后的晚餐?怕哪个谁和谁谁难堪?让钱让权玩了个团团转,歪歪心眼,理得心安?人在做,主――在看!那跟狗玩的小孩儿倒是衣冠楚楚,可他妈的他妈不该和他一起还没隔离完?矫局长说他不知道,没羞没臊,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那么多摄像头,狗都能把耗子捉住,里面的弯弯道道鬼知道他妈的来路?国外混不下去啦?国内关系过硬啊!吃里扒外,没皮没脸,半夜吸血的蝙蝠,排泄也传染――病毒!”
“具体到个人的情况咱们都不清楚。”
“算了吧,牛老师。一到这种时候你们该怎么说,我都一清二楚!”
“你应该清楚在现在这种情形下,咱们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个乱动,全部乱套,谁也跑不了。”
“那是我死了以后的事喽!”
“人在做,天在看,天,什么不都清清楚楚?”
“主,爱每一个人,是――主!”
“这不就得了!吃上感冒药,好好睡一觉,那看门老头一定不让你报到。”
“你是说撒旦,还是圣约翰?”
“嗯――都不认得。您看着办!”
“那好,哪就?”
“再,见。”
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lzxmw777